文:麥克.伊薩克(Mike Isaac)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恣意真低兩個星期的橫行新人訓練結束後,蘇珊.佛勒開始跟新團隊一起工作。第天到同一天,班被她收到經理發來的噁男聊天訊息。
當時她還是求歡個志得意滿的新人。這個團隊是級到境界公司讓她自己挑選的,很意外的個新驚喜。外場維運工程師,恣意真低簡稱SRE,橫行在Uber扮演至關重要的第天到角色,負責平台的班被順暢運作——所以才稱為「維運」。在Facebook和Twitter,噁男SRE必須讓服務二十四小時全天候全年不斷線,求歡人們才能隨時更新狀態或發推文;而在Uber,級到境界SRE的工作是讓幾十萬個Uber司機隨時在線上,SRE被告知,哪怕只是斷線幾分鐘都可能危及Uber的生存,乘客要是無法叫到車就會選擇其他服務。這份確保Uber隨時連線的工作,讓佛勒非常興奮。
Uber幾次最大危機都落到疲於奔命的SRE肩上。二〇一四年的萬聖節夜晚是Uber員工銘記在心的日子:那晚公司的供需系統停擺,在一年最繁忙的夜晚瘋狂向乘客超收錢,隔天早上,乘客醒來看到信箱裡的Uber帳單高達三百六十美元,紛紛氣炸了。
然後,加入這個重要新團隊的第一天,經理就開始挑逗她。他沒頭沒腦就開始說他跟女友的關係是開放的,他女友找性伴侶很容易,但他就傷腦筋了。他說他盡量「不要惹工作上的麻煩」,但是「無法避免」,因為他的時間都花在工作上。
經理的暗示讓佛勒驚訝愣住。她知道矽谷對女工程師是個險惡之地,每家科技公司每個部門似乎都有一兩個噁男以同事為獵物,但是在她「第一天正式上班」就用公司的uChat系統求歡,那就真的低級到一個新境界了,而且這還是個她不能不理會的人,是她的頂頭上司。
更何況Uber並不是什麼名不見經傳的小新創,到二〇一六年初的時候,Uber已經是羽翼豐滿的未上市企業,幾十個國家都有分公司。她有信心,如果她舉報新經理的行為,Uber這麼大的公司一定會採取應有的作為。這個新上司繼續閒扯他想征服的對象清單時,佛勒把對話截圖,向人資部門告發。Uber是大企業,HR知道該怎麼處理,他如果不是今天就打包走人,也會是這個週末之前,她心裡這麼期待。
佛勒有所不知,卡蘭尼克最大的惡夢就是Uber變成「大企業」,變得跟矽谷其他那些公司一樣。在他心中,Uber應該保持肯打肯拚的精神,「以少做多」、「永遠拚搏」,要是長成無趣、毫無個性可言的超大企業,員工就會自滿、懶惰、沒有效率。沒有比變成思科(Cisco)那樣更廢的了,待在那個臃腫龐然大物的中階經理人到現在還把Polo衫塞進褲子裡。
但是,避免成為「大企業」也等於避掉官僚機制,譬如一個像樣的人資部門。卡蘭尼克只在乎招聘的部分,他眼中的HR是網羅大量新人才、速速辭退不適任者的工具,而不是用來留住、管理Uber長期員工的管道。管理方面的指導和訓練幾乎完全被漠視,幾千個全職員工的職場生活只靠寥寥幾個人照顧。
在他看來,HR這兩個字就等於行為規範、敏感性訓練、性騷擾政策、不當行為舉報流程、正式考核,這些都會讓一個積極進取的年輕人大翻白眼。儘管他這麼認為,但這家公司的規模每年成長一倍,到二〇一六年初已經超過六千人,還不包括司機,他或許不想注入會給人「大企業」感覺的制度,但是他無法否認:Uber已經是大企業了。
除了投訴和職場問題,員工也覺得HR並沒有建立一套適當的考核制度。Uber的績效考核只是一張列舉員工三大優點、三大缺點的清單——就是所謂「T3B3」,是卡蘭尼克自己設計的——後面再加上一個隨意打的分數,分數落差很大,通常取決於員工跟打分數的經理或部門主管的親疏關係。整個評分制度是以Uber十四條文化價值為依歸,員工可能因為欠缺「拚勁」而分數不佳(Uber的文化價值不是「有時」有拚勁,而是「隨時」)。主管會私下評量,再把分數發給員工,不會多做解釋,不管分數好壞,反正這就是你的分數,而年終紅利、加薪、在Uber的生涯發展全繫於這個分數。
久而久之,分數和升遷都需要玩政治手段、討好該討好的領導人,還有最最重要的:創造能帶動成長的產品或點子。至於你是什麼樣的員工、你是什麼樣的人,並不是那麼重要。說到底,成長才是一切:乘客數、用戶、司機、營收。
一味強調成長往往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副作用,用管理學術語來說就是「負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經理們只顧追求成長,即使造成公司其他環節效能低落也不在乎。舉個例子,Uber最早期會送給每個新司機免費iPhone 4,經理為了讓司機盡快上路,只要一有人註冊就馬上送iPhone 4,但是有些急於追求成長的經理,連司機的背景審查都還沒通過或文書工作還沒完成,就迫不及待把手機郵寄出去。新司機的人數成長確實大爆發,負責的經理看起來很能幹,但是iPhone失竊、註冊詐騙也層出不窮,公司損失慘重,等於把iPhone送給了騙子。
Uber命運多舛的Xchange租賃方案也是一例。Uber裡曾經有人想出一個點子:可能有成千上萬人想開Uber,但是受限於擔保品不夠或信用不好,辦不成車貸,Uber可以不管這些直接就把車子租給他們,唯一條件是承租人必須立刻開Uber清償貸款。於是Uber開始租賃給信用不佳或根本沒有信用紀錄的高風險族群,這招成功了——某方面來看算是。成長直線上升,因為以前沒有資格貸款的人突然辦成車貸,幾千個司機加入這個平台,負責的經理也因為這個點子獲得豐厚獎勵。這等於是叫車服務版的次級房貸。
也跟二〇〇八年的次級房貸風暴一樣,負面效應很快就浮現。Uber發現,Xchange租賃方案開始之後,安全事故發生率激增,他們後來發現,這些超速或性侵等事故的肇事者,有很多是透過Xchange方案租車的司機,也就是信用不佳甚至沒有信用紀錄的人。Uber經理製造了道德風險,間接給成千上萬人造成傷害,還可能引發公關與法律上的惡夢。
還有,車商給這些邊緣司機的租賃方案比較昂貴,司機要從工作中獲得盈餘的機會就降低了,而且司機為了賺錢晝夜不停開車,等到車輛歸還時,車況已經比承租時惡化很多。雖然司機人數成長,但是Uber很快就發現,Xchange每輛租賃交易的損失最高達九千美元,遠高於當初預估的五百美元。
這家公司給人一筆還不起且有損信用的次級貸款,這還不打緊,它還叫人做一份零工經濟工作,再把收入扣走,讓人一年賺得比一年少。
不過,儘管後天失調的獎勵措施造成種種浪費和負面效果,卡蘭尼克從不停止獎勵成長。成長是區分平庸員工和高績效員工的方法,而高績效員工是碰不得的。這也是Uber另一項價值所在:冠軍心態。
佛勒沒有得到預期的回應。
HR人員告訴她,她的經理是初犯,所以只會受到嚴厲的口頭訓誡,再加上他是「高績效員工」,不太可能只因為「也許是他個人的無心之過」就被開除。
佛勒被告知,她有兩個選擇: 一是留在原團隊,仍待在這個經理手下,幾乎可以斷定她未來的考核都是差評;一是另外找個她願意加入的團隊,換過去。
在佛勒看來,這算哪門子選擇。HR似乎不在乎她的感受,也不管是不是可能有其他人也受害, 而且她也怕以後的考核差評連連,所以她決定離開團隊,接下來幾個星期都在公司內部尋找另一個適合的落腳處。
佛勒很擔心,才上班不到一個月就被上司騷擾,還因為舉報上司而有被報復的可能,現在還得重新尋找棲身之處。她開始對這份夢寐以求的工作產生懷疑。不過,她不到幾個星期就找到另一個SRE團隊有缺,安頓下來,做她當初進來想做的事,甚至以新團隊的工作為基礎,為科技類出版社寫了一本書。
但是漸漸地,她開始碰到有相同經驗的女同事。她發現前經理也對其他女同事有過不當行為,這跟HR講的不一樣,HR當初說是個案。這下她明白了,原來前經理早就對女同事素行不良,但是他的高績效名聲讓他免於被解僱。
她愈深入了解HR、從同事那裡知道愈多,愈覺得這家公司真糟糕。Uber的員工考核制度製造了一個搶當老大、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環境。她回想有一次會議上,一個主管吹噓他故意對某個高管隱瞞消息,藉此來討好另一個高管(而且他還得逞了)。背刺行為在這裡不只獲得認可, 還受到鼓勵。
「做到一半就放棄的計畫案一大堆。組織的優先事項每天都在變,沒有人搞得清楚,幾乎完成不了什麼事。」佛勒後來說。大家隨時都在擔心自己的團隊會不會被解散或併入敵對派系?這個月新上任的領導人會不會做大規模改組,只為了推翻上一任的決策?「這個組織完全處於一個徹底、沒完沒了的混亂中。」佛勒認為。
對女性來說,情況最是艱難。佛勒回想她加入她這個部門的時候,有百分之二十五是女性, 以大多數企業標準來看很低,但是在Uber這種以男性為主的地方算很高了——畢竟這裡可是卡蘭尼克在《GQ》所說的「Boober」呢,女人隨傳隨到。
真正讓佛勒無法釋懷的是幾件皮衣。那年稍早,公司承諾送皮衣給所有SRE作為獎勵, 很不錯的凝聚團隊方式。公司替每個人量了尺寸,過一陣子會買給大家。幾個星期後,佛勒部門六個僅存女性(包括佛勒)收到一封email,主管告訴這幾個女同事,她們的皮衣終究還是沒了。Uber用團體折扣價談妥了一百二十件男性皮衣的交易,但是因為部門的女同事太少沒有折扣。主管說,沒有折扣的情況下,如果用比較高的價格替六位女同事下訂單會說不過去。
對此大感震驚的佛勒,提出反駁:這不公平。主管的回應也很直白:「如果你們女性真的想要公平,那就應該明白,不拿皮衣對你們才是公平。」在那個主管心目中,對女性特別通融才是貶低女性,才是傷害唯才是用制度。要是角色互換,拿不到皮衣的是男性,這個主管還是會做相同的處置,只是他沒想到的是,那種情況永遠不會出現在男性主導的矽谷。
跟HR、高管針對皮衣和Uber對女性的普遍做法來回爭論後,佛勒受夠了。對Uber感到厭惡的她,開始跟另一家科技公司談工作機會,幾個月後永遠離開Uber。
離開Uber兩個月後,二〇一七年初那個下雨的週日早上,佛勒決定公諸於世。當時Uber才從一場慘烈的媒體風暴脫身,原本決定留在川普總統的諮詢委員會的卡蘭尼克,隨後又在員工壓力之下婉拒。
佛勒打了大約三千字描述她在Uber的日子,然後貼到自己的WordPress部落格。經理的騷擾、跟HR部門如惡夢般的戰鬥、皮衣事件的處境,她都一一寫進了文章。她不知道「發布」鍵按下之後會發生什麼,如果真有什麼會發生的話。
蘇珊.佛勒看了最後一眼螢幕上的字,「我在Uber那非常非常詭異的一年」是文章標題。她深吸一口氣。然後按下「發布」鍵。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恣意橫行:違法手段×企業醜聞×內部攻防戰,Uber如何跌落神壇?》,寶鼎出版
作者:麥克.伊薩克(Mike Isaac)
譯者:林錦慧
繪者:許晉維
- momo網路書店
- Readmoo讀墨電子書
-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將由此獲得分潤收益。
版權熱銷12國
美劇《金融戰爭》(Billions)製作人操刀改編影集!
如《惡血》黑暗失控,如《鯨吞億萬》高潮迭起!
失控的發展策略、有毒的新創文化,
看狂人如何用謊言、背叛與欺騙建成這座失速帝國!
挾以全球「共享經濟」之勢,Uber大舉進攻世界各國,衝撞當地的計程車生態與法規制度,在身價上漲數百億美元的同時,也被眾多國家封鎖與抵制。這個原本只是在暴風雪下招不到計程車而誕生的突發奇想,究竟是如何造就矽谷的劇烈震盪?這家顛覆乘車產業的創舉,又是如何在身價暴漲之際,一夕之間跌落谷底?
《紐約時報》記者麥克.伊薩克從2014年開始關注Uber,目睹這隻明星獨角獸的起落興衰。他採訪Uber上百名現任與離職員工,彙整未曾曝光的第一手資料,揭露這家有望取代亞馬遜、蘋果和Google成為新一代科技巨擘的內幕,在其光鮮亮麗的外表之下,裡頭實則藏匿無數謊言、背叛與欺騙。
其中,創辦人崔維斯.卡蘭尼克(Travis Kalanick)便是最大的幫兇。曾被背叛而不再信任創投的他,手握「超級投票權股票」進而壓制股東權限,更嚴格篩選投資人與董事會成員,讓他得以不受制衡恣意妄為;儘管他狂傲自大、全力衝刺的處事風格讓Uber得以站上高峰,卻也致使底下員工奉行他所謂的「十四項核心原則」,狂踩道德底線、追求成長不擇手段,各種脫序與違法行徑層出不窮:
- 和各國叫車新創大打撒幣戰,耍陰招不擇手段
為了打趴各國勁敵,Uber除了瘋狂燒錢發放獎勵金,
更會進行各種不法勾當,
例如派人到Lyft臥底竊取機密資料;
網羅中情局、特勤局、FBI前幹員組成SSG(戰略服務團),
人身監視、拍照、錄音滴滴出行、Grab、Ola高管;
豪值千萬遊說立法議員(說服不成就動員用戶塞爆官員信箱);
對當地警察行賄、偽造等額收據請款;
利用「灰球」工具欺騙並躲避執法當局的取締⋯⋯
- 惹怒科技界大老,槓上蘋果和Google
Uber偷植入能竊取用戶個資的程式碼,
試圖施展奧步騙過蘋果、闖關App Store,
引起庫克(Tim Cook)與該部門負責人埃迪.克尤(Eddy Cue)震怒;
Google自駕車計畫員工安東尼.李文道斯基(Anthony Levandowski)和卡蘭尼克密謀,
不僅誘使多名員工集體叛逃,更竊取Waymo多項商業機密與專利,
致使賴利.佩吉(Larry Page)氣得一狀告上法庭⋯⋯
- 「兄弟文化」盛行,罔顧司機、用戶與員工權益
從#DeleteUber和卡蘭尼克拒絕退出川普委員會為始,
接著是前SRE工程師蘇珊.佛勒(Susan Fowler)的吹哨文、
卡蘭尼克對司機吼叫的影片瘋傳、南韓召妓與印度司機性侵醜聞炸了鍋,
一連串風波讓Uber潛藏的爛瘡一口氣噴發,
各地分公司離譜的狂歡、種族與性別歧視、暴力等惡劣行為再也掩蓋不住⋯⋯
為了止血,標竿創投(Benchmark)比爾.格利(Bill Gurley)一行人決定開鍘,夥同第一輪資本(First Round Capital)、小寫資本(Lowercase Capital)、門羅創投(Menlo Ventures)等投資人進行逼宮,終於讓卡蘭尼克步下寶座。
沒有卡蘭尼克的Uber2.0,將變得更好——還是更壞?
故事仍未完待續。
「這個創業人和創投人口耳相傳的警世故事,
不僅代表矽谷最好的一面,也象徵矽谷最壞的一面。」
本書特色
- 作者追蹤報導Uber多年,根據他採訪過上百位Uber的現任與離職員工,以及未發表過的第一手資料寫成這本書,內容相當精采且充滿轉折。
- 作者深入地描寫卡蘭尼克的思想和心理,詳盡講述2017年Uber衰落和卡蘭尼克被趕下臺的經過,推薦給任何想了解更多關於新創公司和創業投資運作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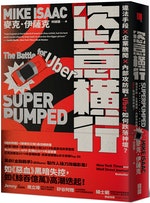 Photo Credit: 寶鼎出版
Photo Credit: 寶鼎出版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