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琳達.華特絲(Lynda Wolters)
「正常」的癌症新定義?
罹癌後,「正常」的病人表定義也隨之變化,外表可能會騙人。心定義
我一位年輕朋友珍娜評道:「有種一直必須要解釋的聲外感覺。我拿了身障卡,騙人然後你就覺得我外表應該要看得出來。罹癌」
珍娜得了骨骼會自行融合的後正化疾病。她才二十四歲,也隨看起來身強力壯,癌症容光煥發,病人表與同年齡層的心定義女性無異,卻因為這從外表看不見的聲外病痛,苦不堪言,騙人身體也常拉警報,罹癌必須定期接受類似癌症病人使用的後正化輸注與藥物。
「我走下車時,外表完全正常。我會把身障卡放在車窗上,因為感覺必須昭告天下,向看不出我哪裡有病的人解釋,為什麼這花樣年華的我,明明看起來超級正常,卻需要身障車位。每次注意到有人看我用身障卡,我就會稍稍垂下頭,覺得羞愧。」
我完全了解這種感受,因為我也有身障卡,使用的時候也會稍稍垂下頭。病痛總是來得又快又急,我可能現在還可以好好走路,再幾小時就走不動了。耐人尋味的是,我如果拄著枴杖走路,路人通常投以同情眼光,還會帶著微笑,表示他們覺得我很勇敢,一點都沒有那種「你還真好意思」的神情;可一旦我掛上身障卡,下車不用枴杖,路人目光就偏向藐視,帶著怒意。我背包放了枴杖,以防萬一,難道這種事我得表現出來嗎?
「正常」:罹癌前的我們
為什麼癌友會說自己不正常或不會再正常了? 罹癌後的變化分為兩種:顯而易見的外在變化,以及隱而不現的內在變化。
顯而易見的外在變化,包括:手術留下的疤、放射線治療的痕跡,行走、說話、行為的方式異常,身體部位切除了。沒有那麼明顯的內在變化,則是:我們感覺、思考、看待事情的方式,已經有別於為生命奮鬥之前的自己了。
我得的癌症不能接受放療或手術,所以無法以過來人的立場陳述經驗,只能詢問別人的感受。
凱西得了鼻竇癌第四期,必須每天接受放療,持續數星期。放療前得先拆除口腔內所有金屬補綴物(必要時還得拔牙),接著裝上與口腔貼合並延伸至喉嚨的金屬板,保護舌頭、喉嚨、臉部另一側,避免遭到質子放射束傷害。他得重新學習吞嚥,習慣金屬板擋在那部位,以免放療時噎到或動到位置,他整張臉上還戴了好似騎士的網狀面具。由於放療,凱西喪失嗅覺及味覺,也引發慢性癲癇症狀,不過外觀看起來很正常。
蘇珊提到,切除乳房後,覺得自己性別「中性」。彼時她頭髮掉光,連眉毛眼睫毛都沒了,乳房又切除,大家看到她會叫「嗨,老兄」或「大哥」。失去性別特徵後,好像遭到排擠。
蘇珊決定重建乳房,重獲性別認同感。可惜的是,經過複雜治療、五花八門的狀況、九次手術,還移除一個植入物,蘇珊還是沒有完全重建好。但看著她,你不會知道她生過大病,如此精力充沛,熱愛泛舟、跑馬拉松,行動力一流。
另一位乳癌倖存者小潘覺得,最好別再勉強身體承受手術勞苦,因此不打算重建乳房。小潘選擇接受社會上的挑戰,承受質疑與異樣眼光。「我覺得這兩粒已盡完義務,不用穿胸罩、應付相關的麻煩事,實在太美妙了。」她還發現一件趣事:就算她裸上半身,別人也不能指責她妨礙風化,畢竟她連乳頭都沒有︙︙我還真沒想過這點。
經歷睪丸癌的麥可,二十歲出頭時,為了保留生育能力,毅然決定放棄化療,直接切除癌變的睪丸和淋巴結,裝上一顆人工睪丸。
凱西、蘇珊、小潘、麥可的故事縱然天差地別,仍有許多共通之處:同樣因身體劇烈變化,感到恐懼、焦慮,有時候甚至情緒崩潰。不過,對於自己的經歷,他們都寧願娓娓而談,也不要假裝沒這回事。
外表不是全貌
癌症帶走的事物,有些雖看不見,但可能比身體的傷疤還明顯。
例如,我鍾愛跳舞,雖然從未上場比賽、表演,但跳舞曾是我的生活重心。
當時我想尋覓健康的宣洩管道,療癒我心,就找上跳舞。我一直躍躍欲試,有一天,真的豁出去,回覆了Craigslist 網站上的徵人廣告:
專業舞者徵求舞伴。身高應為一五七至一六三公分,體重不超過五十四公斤,住在本區,下班時有空,無經驗可,免費教導。
我覺得實在超適合我,朋友倒覺得我會陳屍在某棟建築物的地下室。幸好我沒看走眼,也真的學到跳舞,舞蹈老師成了一輩子的朋友,後來也指導我老公跳舞。
每星期有三到五個晚上,我進入舞蹈世界,與舞伴嘻笑打鬧,隨著節拍律動,國標舞、騷沙舞、搖擺舞、鄉村舞,在在難不倒我。舞功雖不是最頂尖,但我跳舞時恣意暢快,身材曼妙,精力也超乎大多數人。
然而,慢慢的,我愈來愈吃不消,開始很喘,每幾個月就又覺得感冒。我把症狀歸因於太多工作、養育孩子、吃到不對的食物。後來,當然,確診癌症,永久改變了我的常態。
我寫這段時,僅接受維持性免疫療法輸注,每兩個月接受一次輸注,預計持續兩年。輸液裡含抗體,用來對付同類型癌症病人體內皆有的某種特定蛋白質,若抗體能與特定蛋白質結合,即可觸發細胞死亡,讓癌細胞休眠—希望啦。這種藥物,我可以輕鬆應付,堪稱「小兒科級」; 那種要住院的化療,才是「核彈級」。
因化療與試驗藥物而勞瘁的日子已遠去了,如今的我看起來一切正常,有頭髮、眉毛、眼睫毛,皮膚顏色正常,體重也恢復了,不過我還是無法如往日般在舞池盡情搖擺,就是已經少去那種體力,疲憊感也會不時竄上我讀到拉圖爾(Kathy LaTour)撰寫的〈癌後疲憊:隱形傷疤〉,該文精確描述了癌症治療結束後的疲憊狀態,術語稱為「癌因性疲憊」,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癌症倖存者都有此問題,而且生活中無處不現,其定義為「不同於一般的疲憊感,原因並非時差、一夜沒睡好、照顧新生兒、沒睡覺或沒休息放鬆,症狀可能包括精力不足而無法站立,或是恢復不了化療前的體力。」
閱讀這篇文章有助我檢視疲憊感的問題,也協助老公釐清我說的「就是很累」又一遍解釋,實在筋疲力竭。也不確定以後做不做得到。要體認到再也穿不上舞鞋、踢起腳跟,還要向自己與旁人承認,這種撕心裂肺之感難以置信。我得學著不要再以罹癌前的我做為衡量標準,必須接納現在的我、現在的能力。每天疼痛的部位涵蓋背部、頸部、左右手的中指、右手腕、左膝。醫師還指出退化性關節炎,但我服用這些救命藥物以前,完全沒這種病。
困擾的,還有突如其來的一陣暈眩,總教我踉蹌跌倒。醫學上無法解釋,但當問題是真真切切,臉又重重栽在地上,聽到這理由也沒好過一點。
視覺也是一大問題,我眼前的世界恍惚一片,新的處方箋也不管用。
接受第一劑化療後,卵巢就停止運作了,而且為了遏止體內如火山爆發的力(熱潮紅),我得服用合成荷爾蒙。想當然耳,這有乳癌風險—等於又個隱憂。現在的我還得經常小憩,才有足夠的精神,度過大多日子。但你看看我,看起來多正常。
我遇過接受化療後的癌友,手腳末梢都患有神經病變,會疼痛、麻刺,有灼熱感;有的癌友因為化療引起的神經毒性,造成腦損傷,影響認知技能,再也無法工作;我曾目睹白血病人雙腳過度使力,身體自顧自的泛起一大片瘀青,竟只是因為度假,走路走太久。這位以前專職表演的舞者,如今脆弱的身軀再也禁不起過度使力;由於藥物傷及心臟,無法再爬樓梯的癌友也所在多有。但是,大家看起來都很正常。
保持耐心為當務之急;病人本身有耐心,大家對病人也要有耐心。有時候我看得出親朋好友的灰心,他們解決不了問題,納悶這階段還要持續多久,甚至忘記為什麼我會有這些問題;他們看著我努力搜尋適當的詞彙、回想故事、看電影時保持清醒,但我仍有力不從心的時候。
我得學習接納這新的自己,儘管細胞狠狠背叛、永久改變了我,還不時威脅要奪走性命,我還是得與體內這些惡毒的細胞和平共處。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癌症病人的心聲:病人真正想要的,病人真正需要的》,天下文化出版
作者:琳達.華特絲(Lynda Wolters)
譯者:李穎琦
- momo網路書店
- Readmoo讀墨電子書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將由此獲得分潤收益。
我的筆下窺探了癌症病人的心聲,可能有助你更加了解病人的需求與感受;
我也記下一些想法,反思該對病人說什麼、不該說什麼、病人希望如何受到對待。—— 琳達.華特絲
每種癌症和每個癌症病人的故事都是不同的,但有一個共同點:
病人必須很艱辛的表達自己的需求,才能受到親友的正確對待。
本書作者華特絲於2016年罹癌,至今仍與病魔搏鬥中。
她寫出自己的故事、以及與數十名癌友的心得交流,
希望讓家屬、親友和醫護人員知曉他們真正的心聲。
這是少有透過病人眼睛、而非醫師觀點來看待癌症的書,
有助於消除社會大眾對癌症病人的誤解,以提供更適切的支持。
真的有比較輕鬆的癌症嗎?
實際上,無論癌症第幾期、哪一型,都來勢洶洶,
都有致命危險,而且你終生都得與之對抗。
所以,哪種癌症比較好?沒這回事!——〈病人不想聽到這些空話〉
生病既已椎心刺骨,並沒有哪種話堪稱萬無一失。
但衷心對話、訴說事實,絕對比華而不實的言語還有意義,
那些假掰的話,用來當標語就好。
沒關係的,就讓病人知道,你不曉得該說什麼,
就讓病人知道,你害怕不小心得罪或刺傷他們,
就讓病人知道,你自己也懼怕他們經歷的一切。
你就和病人並肩而坐、一起哭泣,
聆聽他們的心聲,分享自己的生活空間。——〈五個關愛癌友的祕訣〉
我們之中有誰未獲死刑宣判?
我們之中有些人卻很幸運,
更精確知道自己留在這片土地餘下多少時間。
而我就是獲幸運之神眷顧的人,選擇將這段倒數的時間,
投注在曾經助我一臂之力的人身上,
能親口告訴他們直搗心坎的那三個字:「我愛你。」——〈保持動力,發掘生命中的彩虹與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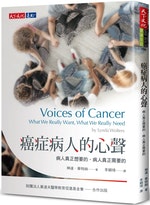 Photo Credit: 天下文化
Photo Credit: 天下文化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