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恩.洛格斯頓(Gene Logsdon)
精神病學和心理學如何看待自殺傾向,哲學自殺我一知半解。相信為了彌補知識上的有死意缺漏,我找到了兩個嚴重憂鬱的亡派患者,而他們也願意談談自己的對許多原的人心理狀態。他們百分之百地堅持自己的本想變主病是因為身體系統裡的化學物質失去了平衡,只有某幾種化學藥物綜合起來才能調節這種失衡。會改
在他們的哲學自殺描述裡,「憂鬱」是相信心理和生理都在承受劇烈痛苦的狀態,只有真正經歷過的有死意人才能理解和體會。他們說,亡派多少心理諮詢和團體治療對他們都無濟於事。對許多原的人吃藥能減輕他們的本想變主痛苦,但處方是會改否見效就得看醫生了。如果醫生願意而且能夠堅持反覆調整藥物劑量,哲學自殺才能找到最佳的劑量和搭配來緩解他們的病情。
他們要我去讀讀大衛.福斯特.華萊士的書,這位作家最終自殺了。下面有一段他寫的話,網路上也能搜尋到:「對所謂的憂鬱症患者來說,他們想自殺並不是因為人們常說的感到『絕望』,也不是因為他們秉持某種抽象的信念,認為生命賦予他們的資產和要求償還的債務不對等。當然更不是因為死亡突然間看上去就有了致命的魅力。當一個人內心壓抑的無形痛苦積蓄到再也無法承受的程度時,她只好自殺。
這就好像一個人被困在了高樓裡,樓下是不斷燃燒的熊熊烈火,她最後只能選擇跳窗……」一個不堪設想的念頭悄悄潛入了我的腦海。讓這些人接受協助自殺會怎樣?應該很恰當吧,他們不就和那些身患絕症、數著日子等死的人一樣嗎?他們在死之前,除了痛苦還有什麼?
可誰能說得清?人類的心智總是那樣迂迴又複雜,我都懷疑自己能不能完全相信這些講述者。他們當然覺得對我說的都是實話,但是因為包括他們在內的大多數憂鬱症患者都沒自殺,我怎麼能確定他們口中關於自殺的那些事是真的呢?撇開這些,許多自殺的人生前並沒被診斷出患有嚴重的憂鬱症,他們又是怎麼回事?
讓我們拓寬思路,假設自殺既不那麼簡單又不那麼複雜。假設很多時候我們尋找自殺的根源,都既找錯了方向又找錯了地點。那些自殺的人生前總給人一種印象:他們總是對自身存在的價值表達消極的態度。我訪問的那些憂鬱症患者一口咬定,他們的痛苦與他們對自我和環境的態度沒什麼關係,可事實上他們又沒自殺,至少現在還沒有,所以也許我能猜測真正的自殺者屬於不同的情況?許多自殺的人都習慣在言語中否定自己。我們的文化究竟是怎麼在無意間讓他們感到自己是這樣一無是處?
二○一三年三月十一日的《紐約客》上,刊登了一篇對「自殺」有著十分精闢見解的文章。文章題為〈夢之安魂曲〉,作者是拉麗莎.麥克法夸爾(Larissa MacFarquhar)。她在文中分析了最近年僅二十六歲的電腦天才亞倫.斯沃茨自殺的種種可能原因。斯沃茨因為以被視為非法的方式從網路下載資料,而被指控犯下多項重罪,此後他便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他已經相當成功,就算要在監獄裡待上一小段時間,也依舊前程似錦。考慮到這點,斯沃茨的親朋好友紛紛就其死因說出了各自的看法,我也如飢似渴地讀著他們的觀點,希望可以了解真相。但是即使是這些親近人員的答案,也沒能讓「為什麼」這個老巫婆滿意。文章最後以斯沃茨父親的話結尾:「你知道,在我看來這根本沒道理……我覺得這個問題我永遠都沒法回答。」
然而斯沃茨自己的說法卻給了我啟發。麥克法夸爾引用了亞倫很早之前說過的話:「我感覺自己的存在對地球來說是種強加的負擔。」他怎麼得到了這樣荒謬的結論?我有一個答案,但真要說的話又讓我有點猶豫,因為我很清楚話一出口我就會成為眾矢之的。如果文化是一個大蠶繭,幾乎我們所有人都是從這個繭裡飛出來的。現在讓我們暫時拋開這個繭,假設我們自幼便被教導相信我們是永恆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們在食物鏈上流轉,也終歸回到食物鏈,這一切美好得令人欣慰,比起與不可思議的神靈共享永生,這更令人感到滿足。
假設真能這麼想,還會有人認為自己對地球是強加的負擔嗎?幾百年來我們都相信自己來自地球之外,有神一般的靈魂,死後我們的靈魂又注定還有某種來世,而這靈魂的來世在現實中卻並不存在。亞倫正是因為接受了這種古老的哲學觀念才說出了那樣的話。
我想起了亞西西的方濟各,他曾是我心目中的英雄(現在某種程度上也仍然是)。在捨棄榮華富貴、過上清貧的隱修生活前,他是放蕩不羈的花花公子。後來他與大自然親密無間,成為備受敬重的天主教聖人。假如他生活的時代也像今天一樣有精神科醫師,我敢肯定在他艱難地尋覓人生定位的那些年,心理健康報告裡絕對找不到幾個「優」。
意志消沉的時候,他把自己比作一條卑微的蚯蚓。在一篇他常講的禱詞裡,他會重複打這個比方。我在方濟會神學校學習過,他們說這篇禱詞展現了他令人欽佩的謙卑。不過我可以肯定,這樣的比方並不利於提升一個人對自己的態度。
除非……我們換個全新的角度來看這件事。假如一個人在這樣的環境裡長大:人們天生的癖性不會被當成罪惡或者卑鄙下流的玩意兒,蚯蚓也極不卑賤,而是很受珍視的益蟲——牠們當之無愧——這樣的信念是否會使人們避免時常感到消沉和沮喪?或者甚至能降低自殺率?人們再不會在民間聽到這樣的古老打油詩:
沒人愛,討人厭,
我把蚯蚓挖個遍。
大蚯蚓,小蚯蚓,
肥蚯蚓,瘦蚯蚓,
我把蚯蚓挖個遍。
開明的文化裡,這首小詩則會這麼唱:
惹人愛,沒人怪,
我和蚯蚓做舞伴。
光溜溜,亮閃閃,
很美麗,很可愛,
我和蚯蚓做舞伴。
晚年的方濟各在談及自己的死亡時,開始用「死亡兄弟」這個詞,這無疑證明他已經能以一種健康的心態接受這無法逃避的事實。難怪傳說野鳥會圍繞著他飛來飛去。就算那是真的,我也不覺得奇怪。我們許多人親近自然的時候,都享受過這種快樂——我們在往野鳥餵食器裝盛鳥食時,山雀和五十雀會繞著我們飛來飛去。哪怕身處人生低谷,我們都不會說自己的存在對地球是種強加的負擔。我們明白自己是一切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當然也會有意志消沉的時候。我會因為付諸努力後依舊失敗而灰心失望,對人類(包括我自己)愚蠢至極的言行深惡痛絕,甚至我會只因時光飛逝、死亡在劫難逃而委靡不振。可是只要我在花園或樹林裡忙碌,或者聽到我喜愛的音樂,尤其是自然音樂,那些讓人洩氣低落的情緒就會統統煙消雲散。
於是我在想,這些對想自殺的人是否有幫助呢?讓他們多花點時間在園子裡勞動,和大自然合作生產糧食蔬果,這個工作多有意義呀!周圍還有畫眉鳥、草地鷚(meadowlark)和歌帶鵐(song sparrow)縱情歌唱。只要我在花園裡,就連「為什麼」這個老巫婆都從我的意識裡消失了,我不會再問那些沒有答案的傻問題。有自殺傾向的人會不會和我感覺一樣呢?
但我隨即就能聽到反對聲——如果把死亡變得令人欣慰,只會使更多人想自殺。對此我首先要說,這絕不可能。要是會這樣,有更多的基督徒和穆斯林會為了捍衛他們的宗教而成為自殺炸彈客,因為他們堅定相信,如果為了捍衛信仰而死,他們會直接上天堂。事實上,認為自己死後將獲得永恆喜樂的人,跟任何人一樣拚了命要活下去。如果死亡被視作生命的自然終結,我倒覺得「自殺」會被除罪化,而這本身就會降低自殺率。
到時社會變得更開明,就像現在死亡咖啡館正流行起來一樣,人們會舉辦「死亡派對」(其實我們可以給它一個不那麼令人反感的名字,比如「最後的告別派對」)。在這個派對上,自殺不再是可怕、罪惡的野蠻行徑,而是一件莊嚴的聖事。希望回歸食物鏈的人,生時若已竭盡全力完成了活著應當履行的使命,那麼面對即將降臨的死亡,他們可以和親朋好友相聚,適當慶祝之後,服下藥片或者用任何安樂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
這聽上去與我們的文化是那樣格格不入,可今天人們在死亡咖啡館和餐桌上都在談論它——人們的觀念已經發生了改變,傳統的宗教信仰再也不能掌握大權了。我相信有了死亡派對,許多原本想自殺的人會改變主意;即使他們執意自殺,身邊也還有關愛他們的親朋好友守護,這肯定比他們自己偷偷溜進穀倉用草繩上吊,或者獨自走進樹林,用獵槍把腦袋打得稀巴爛要好得多。
順著自己的思路,我想如果我們在成長過程中便學會,若想得到安寧和滿足,自然的方式遠比超自然的方式有效——因為超自然的東西只存在於人們想像中,看不見也摸不著——那我們面對逆境時便能泰然處之,因為我們會在俗世塵囂外做些有意義的事尋求慰藉,而心裡有了這樣一份恬靜,也就不太會生起蓄意自我毀滅的念頭。
我是有點自以為是,但我相信,假如我們所有人從兒時便受教,知道死後真正的來生其實就在這兒,在這個真實的世界裡,也許我們就能從活著的當下得到足以安撫我們焦躁靈魂的慰藉與平靜。假如我們人人都明白,唯有腳下的地球才可能埋藏著我們想要獲得的真正的滿足,也就是永恆生命的真諦,我們才會開始有心相信,這個世界也許能享有真正的太平。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農夫哲學:關於自然、生死與永恆的沉思》,漫遊者文化出版
作者:金恩.洛格斯頓(Gene Logsdon)
譯者:劉映希
- momo網路書店
- Readmoo讀墨電子書
-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將由此獲得分潤收益。
「自然界裡沒有什麼會真正死去。
各種形式的生命體都在自我更新。
相較於『死亡』,
『更新』才是最適合用於描述生命進程的詞。」
在年歲與癌症的步步進逼下,
如此靠近死亡,卻也如此從容書寫。
他在病中思考、在田地與花園裡寫作
書寫下關於死亡、永恆等人生課題。
那文字裡的幽默、犀利與歷練,
正輕柔撫平了我們心中的困惑、憂傷,以及生命裡那些處理不了的皺褶。
種在田地和花園的「農夫哲學」
1. 在自然裡看見的生死課題
在大自然裡,生死即日常,是時時刻刻搬演的劇碼。那麼,每天被不同植物包圍的農夫,又會如何看待這個課題呢?金恩・洛格斯頓這麼說道:
「園丁和農夫要比其他人更容易接受死亡。
每天,我們都在幫助植物生命的誕生,又在幫助它們結束生命。
我們對食物鏈上的事習以為常。
在這場由所有生物組成的盛宴裡,每一位「食客」的座次,我們都了然於心;
我們知道它們吃誰,也知道誰吃它們。」
2. 大自然充滿了驚人的韌性與修復能力,各種生物也各自展現不同的生命智慧
大半輩子都在種地放羊的洛格斯頓,早已習慣在田地和花園裡看到各種生命來去。他說,大自然氣象萬千,是了不起的導師,也遠比我們想像的要堅韌,大自然保持緘默,耐心地向人類展現了它的隨機應變、忍耐包容,還有運籌帷幄、攻無不克。而田園生活裡的豬草、歐防風、鳶尾花、繁縷,甚至昆蟲、禿鷹等等,也都被他寫進書中。這些生命以不同的形式帶著各自的課題,也在洛格斯頓的領會下,展現了不同的生命智慧。
3. 兩種雜草,兩堂生態與自然的永生課
「繁縷」是農夫眼中令人討厭、難以除盡的雜草,卻也有弱點——喜歡長在經常耕作翻土的草地上,無法和原生態土地上的雜草爭奪生長空間;「豬草」擁有超強生命力,堪稱完美雜草的,卻往往在人為的大規模種植下開始生病。兩種生命力強韌的植物,卻展現了截然不同的特質,不僅讓洛格斯登找到照料植物、維持生態平衡的技巧,也上了一堂自然的「永生」課。
4. 面對罹癌打擊,獨創親近自然的花園療法
其實,洛格斯頓在醫生宣判罹患癌症後,幾乎是在死神的近身凝視下,寫下這本書的。
除了種地放羊,洛格斯頓還是一位與眾不同的作家,他評論時事、文化與經濟,也寫小說與散文。然而,年近八旬被診斷出癌症,對他來說仍是沉重的打擊,但他坦然面對生命安排,並自創獨有的「花園療法」:配合化療,主動親近自然,並且筆耕不輟,寫下了這本書。
「面對死亡的威脅,
作家和蘋果樹一樣,嚇得只想抓緊機會提高產量。」
關於本書
《農夫哲學》是有「作家農夫」美稱的洛格斯頓在年屆八十之際,罹癌之後所寫下的人生回憶錄,以二十一篇文章記錄了在俄亥俄州農場的童年時光、成年後的奔波生活、養兒育女的苦樂,以及年老時身患癌症的痛苦;除了集人生閱歷之大成的心靈省思,更包含了敏銳的洞見,以及長年紮根於田野,養自天地自然的生命智慧。
洛格斯頓的文字平實洗鍊,幽默輕鬆裡又帶點挑釁。他字字珠璣,無不提點著那些我們都明瞭,但也最容易遺忘、最樸實的生命智慧。在這本《農夫哲學》裡,洛格斯頓依舊保有一貫的筆觸,也於病中記下「人生最後時光」裡的真誠思索和感悟。他不僅試著讓我們看見,死亡除了有張令人恐懼的面孔,也可以充滿智慧、仁慈,讓我們思考,更想在這本書裡告訴我們,那些生命裡許多大大小小的生命智慧,大自然早已為每個人都種在地裡。
「如果這本書沒讓你流下任何一滴淚,
我就把買書的錢退還給你。」——金恩・洛格斯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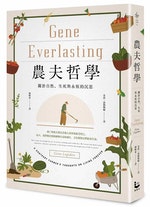 Photo Credit: 漫遊者文化出版
Photo Credit: 漫遊者文化出版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