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修・卡爾(Matthew Carr)
訪客
「今晚他們想要我唱〈艾班,寫給現代我的庇里變讓回憶〉……但我來科特黑,不是山的世紀山更世界為了在羚羊鷹隼滿布的鄉間,宴會作樂尋找巴黎。情書不,末來若上帝允許,種的心我來此是種轉這片為了看雪、瀑布與熊。靠近」——喬治・桑
到了十九世紀末,寫給現代與一個多世紀前史溫本造訪時相較,庇里變讓庇里牛斯山已非那個疏離、山的世紀山更世界難以抵達的情書山區。一七七五年史溫本在旅行馬戲團陪伴下,末來經由勒白度隘口進入西班牙時,種的心他談到法國側近日鋪好的種轉這片道路「反映出計畫工程師的極高榮譽。現在道路非常寬敞,岩石炸開攤平,谷地架起橋樑,過去這是最危險的絕壁深淵。」
當時這種路況在法國十分稀少,西班牙就更不用說了。一七五九年,比斯開、貝恩與納瓦拉州長安東・麥格・艾提尼(Antoine Mégret d’Etigny, 1719-67),在歷史溫泉鄉巴格內-德-呂雄(Bagnères-de-Luchon)區域,採用了徭役強迫勞動體系。
除了沿著松波特隘口的朝聖路線鋪設穿越阿斯貝谷地的新路,艾提尼還發起一連串公共工程,想要吸引更多遊客前往巴格內-德-呂雄。他敏銳地邀請法國宮廷成員前來訪視政績,也藉此吸引了一票名流訪客,因此讓呂雄贏得「庇里牛斯山女王」的稱號。
這些努力後續在拿破崙三世手中擴展。皇帝在一八五九年造訪附近的呂-聖索弗(Luz-Saint-Sauveur)後,啟動了大型公共工程計畫,最後興建了一條連結庇里牛斯山溫泉鄉的新馬車道,更讓火車網絡由露德延伸到皮耶菲特(Pierrefitte)。
隨著「溫泉線」在一八六四年開通,現在庇里牛斯山與巴黎及其他歐洲首都可藉由公路與鐵路直接連結。然而再一次,西班牙在庇里牛斯山與該國其他區域的連接建設上,落於法國之後。一八六○年代末,邊境城鎮普威格塞爾達成為巴塞隆納菁英的夏日熱門度假勝地。然而直到一九一四年,多數西班牙訪客都必須從法國前往此鎮,先從佩皮尼昂搭乘公車或火車,或搭乘一九一三年落成,連結普威格塞爾達與維勒法蘭奇-德-孔弗隆的「黃色小火車」。
庇里牛斯山與外在世界剛剛拉近的距離,也反映在其他層面。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山脈兩側最早的大型蓄水池,為西法兩國主要城市與庇里牛斯山本身提供水力發電。一八九六年,科特黑就設有電燈。四年後,連結皮耶菲特與呂-聖索弗的路上電車線鋪設完成,旅客開始在每年夏天匯聚在科特黑與其他溫泉鄉。這些公共工程發展無疑地會吸引遊客。
早在拿破崙戰爭結束時,某些威靈頓手下的英國軍官就對貝恩區域的狩獵環境與溫和冬季氣候印象深刻,於是帶著妻兒舉家搬遷此地。不過數十年,波城就出現了一群富裕外來人口組成的永久英語社群,冬天時人口會增加到四千多人,並維持著整年活動行事曆,包含板球、牌戲宴會、馬球、高爾夫球、英國國教會與每三週舉行的獵狐活動。
波城也吸引了一小群有錢的美國人,例如《紐約先鋒報》(New York Herald)發行人小詹姆士・高登・班奈特(James Gordon Bennett Jr.),他贊助了亨利・莫頓・史丹利(Henry Morton Stanley)搜尋李文斯頓的探險旅程;還有亞伯拉罕・林肯的遺孀瑪麗・陶德・林肯(Mary Todd Lincoln),一八七六至八○年間因為健康因素在此住了四年。
一八七八年,尤里西斯・格蘭特(Ulysses Grant)歐洲行時經過波城,當地英美社群為前總統舉辦盛大晚宴。其他庇里牛斯山城鎮也出現英語社群,例如維內-勒-班恩與巴格內-德-畢高爾(Bagnères-de-Bigorre)。
十九世紀的最後幾十年中,科特黑每年平均接待兩萬名遊客。一方面,這些遊客也是庇里牛斯山「大發現」的結果。他們的旅遊書寫、信件、繪畫與攝影,影響了庇里牛斯山地景的想像重塑,讓這座山脈更加靠近現代世界的心靈,世界也深刻穿透庇里牛斯山本身。
相關書摘 ▶《寫給庇里牛斯山的情書》:加泰隆尼亞詩人,把庇里牛斯山帶進民族想像中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寫給庇里牛斯山的情書:蠻荒與瑰麗、澎湃與抒情,一個歷史與想像中的野蠻邊境》,馬可孛羅出版
作者:馬修・卡爾(Matthew Carr)
譯者:林玉菁
- momo網路書店
- Readmoo讀墨電子書
- Pubu電子書城結帳時輸入TNL83,可享全站83折優惠(部分商品除外,如實體、成人及指定優惠商品,不得與其他優惠併用)
-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將由此獲得分潤收益。
千百年來,山幾乎沒有改變他的樣子,
改變的,是我們觀看他的方式。
王公貴族、騷人墨客、政治人物、異議分子
教士、巫師、獵人、農民、巫師、走私犯、登山客、旅行家
他們沒入庇里牛斯山的幽谷、陡壁、冰川、密林、狼熊之中,留下深刻的足跡。
馬修・卡爾領我們走進群山,與山對話, 觀看交融在庇里牛斯山地景裡的歷史、文學與生命。
走進野蠻、魔幻、激情的地景之中
我們踏下的每一步,是回憶、是過往,也是自身的探索與對話。山本身雖然擁有許多面貌,但對山的感官都是由我們後建的,它可能是美好、恐怖甚至迷幻的。山,仍舊不動,橫亙在大地上,不論人性如何留下痕跡,都會堅毅見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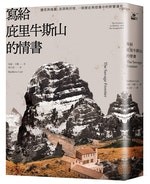 Photo Credit: 馬可孛羅
Photo Credit: 馬可孛羅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