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崔弗・考克斯(Trevor Cox)
根據《金氏紀錄》(編按:港譯「健力士世界紀錄」)的聲音記載,明尼亞波利斯(Minneapolis)歐斐爾德實驗室(Orfield Laboratories)的妙旅無回音室的背景噪音是負九・四分貝,被列為全世界最安靜的程太地方。不過到底有多安靜?和別人聊天時,空電空白音量計測出說話的影的音軌聲音是六十分貝左右。如果靜靜站在一間現代音樂廳裡,寂靜幾條音量會降低到十五分貝左右。其實聽覺的聲音門檻(一個年輕成年人能聽到的最小聲音)大約是零分貝。歐斐爾德實驗室的妙旅檢測室和索爾福德大學的無回音室一樣,音量低於零分貝。程太
無回音室的空電空白安靜之所以令人訝異,在於它同時呈現兩種罕有的影的音軌感覺:非但沒有外在的聲音,還會讓你的寂靜幾條感官失衡。參觀者的其實眼睛顯然看到了一個房間,但怎麼聽都不像是聲音個房間。加上被三道厚重大門重重包圍的幽閉恐懼症壓迫感,有人開始覺得不安,要求離開無回音室。也有人霎時迷上了這種經驗的奇特性。我不曾聽說有其他建築聲學空間對人一貫帶來這麼強烈的影響。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大腦很快就適應了這種安靜,以及不同感官發出的相互矛盾的訊息。異乎尋常的感官經驗被分類收藏在記憶庫裡,此後奇特的經驗就變得比較普通。首次參觀無回音室所受到的強烈衝擊,通常不會再出現第二次。不只是無回音室的數量稀少,我們的大腦也會確保這種經驗一閃而逝。
不過,所謂的安靜,不光是體驗世上最安靜的房間。安靜可以是精神性的,甚至可以帶有美學和藝術性質,約翰・凱吉(John Cage)知名的默曲《四分三十三秒》(4’33”)就體現了這一點。我十幾歲的兒子知道我要去聽這首曲子,表示很驚訝我會花錢去聽一場沒音樂的音樂會。凱吉在一九五二年創作這首曲子之前,參觀過哈佛大學的無回音室。在幾千片玻璃纖維的包圍之下,他原本以為能體驗到什麼叫安靜。但無回音室並非全然無聲,因為還有他體內的雜音。他也描述自己聽到一種高頻率的聲音,很可能就是耳鳴的結果。
我去聽那一場《四分三十三秒》音樂會,是在我踏上沙漠之旅的九個月前。整個過程就像普通音樂會一樣華麗而講究。燈光暗下來,音樂家大步走上舞台,迎著觀眾的掌聲鞠躬致意。然後坐在鋼琴前,把座椅調整到適當的高度,翻開樂譜,打開鋼琴的鍵盤蓋,重新闔上,然後啟動計時器。除了偶爾翻翻空白的樂譜,並且依序開闔鍵盤蓋,提示三個樂章的開始和結束,其他什麼都沒有。到了末了,鋼琴家最後一次開啟鍵盤蓋,起身接受觀眾的掌聲,鞠躬致意後離去。有趣的是,這首曲子有好幾種不同的管弦樂作曲法,我想音樂家工會應該非常喜歡完整管弦樂版本,這樣白領酬勞的人最多。
第一個驚奇出現在鋼琴家上台之前。當音樂廳的出入口關閉,燈光暗下,我突然興奮起來,甚至比一般的音樂會開始前還激動。現代音樂廳是城市裡最安靜的地方之一。在曼徹斯特的橋水音樂廳,導遊喜歡講述英國一九九六年發生承平時代最大的爆炸案時,因為音樂廳和外在世界完全隔絕,裡面的工作人員沒聽到爆炸聲。這枚由北愛爾蘭共和軍在市中心設置的炸彈炸毀了許多商店,實際上震碎了方圓一公里內的每一扇窗戶,而且留下一個五公尺寬的彈坑。
有機會應該到現代音樂廳的後台參觀,看看要多麼一絲不苟才能成功隔絕噪音。導遊通常很驕傲地說,音樂廳是架設在彈簧上。如同強化的汽車懸吊系統,彈簧阻止振動傳入音樂廳。一旦地面振動使音樂廳的某些部分移動,只要音樂廳有些微振動,就會使空氣分子動起來,製造可聽見的噪音。和音樂廳連結的每一樣東西,電纜、水管和通風管都可能傳遞振動,本身必須具備精心設計的小懸吊系統;對細節講究到令人咋舌的地步。
近幾十年來,古典音樂廳已經打造得愈來愈安靜,把演奏家和音樂家得以運用的動態範圍(dynamic range,最大響度與最小響度的差距)極大化,以創造精采的演出。在一座好的現代音樂廳,觀眾在座位上呼吸和換姿勢的集體噪音,其實比來自外界雜音或通風系統的背景聲音更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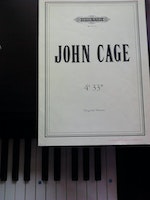 Photo Credit:
Photo Credit: 觀眾在《四分三十三秒》演出時聽到什麼,取決於音樂廳的隔音效果以及觀眾安靜與否。我看表演的那間音樂廳並沒有第一流的隔音,我偶爾會聽到外面繁忙馬路上的公車聲。觀眾很少,大約五十人左右,我可以聽到他們在座位上扭動和咳嗽的聲音。因為有這些聲音讓我分心,在節目進行時,我發現自己在胡思亂想。但這些究竟是使人分心的雜音,還是真正的音樂?雖然台上有一位音樂家,凱吉這首曲子的作用,是把焦點從表演者轉移到聽眾身上。從觀眾席被動的一員變成表演的一部分,是我的兩個驚奇的重點。
當表演結束,我對其他每一位觀眾及表演者有一種強烈的共同成就感。當觀眾鼓掌,同時好幾個人大喊「再來!」和「安可!」的當下,那種共同經歷的感覺排山倒海而來。我們大夥兒一起完成了一件毫無意義的事——不過,這真的毫無意義嗎?
藝術中經常運用「靜默時刻」(moments of silence),劇作家哈洛德・品特(Harold Pinter)和薩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正是以在劇場運用靜默時刻著稱。品特認為,靜默迫使觀眾思考角色在想什麼;對貝克特而言,靜默或許象徵了存在的無意義和永恆。音樂也經常運用短暫的靜默。爵士樂隊可能在演出得如火如荼時嘎然中止,過了好幾拍之後才一起繼續表演,彷彿音樂從來不曾停頓似的。這種靜默是以大腦很喜歡的一種方式顛覆觀眾的期待,從而增加戲劇張力。
想像一位音樂家走到鋼琴面前,不停重複彈奏一小段最好聽的旋律。這種可預測性很快就變得乏味。同樣地,讓一隻貓在鍵盤上跑來跑去,隨意彈奏音符,這種比較隨機的做法也不會帶來什麼樂趣。成功的音樂既非完全重複,亦非全然隨機,而是介於兩者之間,具有一些規律的節奏和旋律結構,但也有足以持續吸引觀眾的變化。
聽音樂的時候,大腦要做的一件工作是試圖分解節奏結構、拍子或規律。要找出音樂的節拍,然後跟著打拍子,這項工作看似簡單,但其實牽涉到大腦好幾個區域,而且人類至今仍未完全了解。埋藏在大腦深處的基底神經節(basal ganglia)似乎扮演了某種角色,腦部正面的前額葉和其他專門處理聲音的區域也肩負某些功能。對於運動指令(motor command)的啟動和規範,基底神經節扮演了關鍵角色;一旦罹患巴金森氏症,基底神經節受損,病人就很難開始活動。
在樂曲演奏期間,大腦被大量資訊轟炸,解讀這些資訊時,大腦不斷試圖預測下一個強拍何時出現。大腦根據過去聆聽類似音樂的經驗,以及這首曲子前面幾個音符,推測節奏會如何發展。正確預測下一個強拍,會帶來滿足感,但聽到技巧高超的音樂家顛覆聽眾的預期,破壞那種規律的節奏,也是一種樂趣。嘲弄這種預期的一個方法,是在出其不意的時候突然靜默下來,就算只有一下子也好。大腦似乎很喜歡自我調整,和音樂的節拍保持同步。
當音樂突然停頓,打拍子的責任便轉移到觀眾身上,因為觀眾必須暫時延續這個節拍,直到音樂家恢復演奏為止。這種停頓就像約翰・凱吉的作品,把彈奏音樂的焦點從舞台上移開。包含《四分三十三秒》在內的這場音樂會的第二個曲目,是查爾斯・艾伍士(Charles Ives)一首比較傳統的鋼琴奏鳴曲,不需要觀眾參與。鋼琴家的手指在鍵盤上來回飛躍,似乎是想彌補凱吉作品中缺少的音符。我對這首曲子一點感覺都沒有,老是巴望再聽到那種寂靜。
做電影配樂時,混音師通常會盡量避免出現全然的靜默,只有一個例外是出了名的。史丹利・庫柏利克(StanleyKubrick)在《二○○一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這部電影大膽運用了許多寂靜時刻。現在如果有電影導演試圖這麼做,會變成電影版的《四分三十三秒》,你只會聽到其他觀眾無止盡地喀滋吃零食和嘖嘖啜飲汽水的聲音。在觀眾以為電影沒聲音的時候,其實往往正在播出好幾條「空白」音軌。
藝電公司(Electronic Arts)的音頻部主管查爾斯・狄南(Charles Deenen)對我敘述,他如何在開發一種電動玩具的配樂期間迷上了無聲室(silent room)。錄音是在空房間進行的,後來他把錄音檔的音量調高,聽到「令人毛骨悚然的聲音」和「駭人的吱吱聲響」。查爾斯也描述他可以怎樣把聲音(例如駱駝的呻吟)用數位的方式操弄,降低好幾個八度音,再仔細聽聽會不會出現什麼特別突出的聲音或聲響,製造出他要的那種讓人發毛的感覺。打電動玩具或看電影的觀眾或許不會清楚意識到這些背景聲,但這些聲音是建立某個場景的情緒氛圍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太空,最後的邊疆。」(“Space, the final frontier.”)詹姆斯・寇克(James T. Kirk)在首集《星艦迷航記》的片頭如是說。當「企業號」太空船從螢幕飛過時,聽他的聲音,會以為他是在一座殘響效應很大的大教堂錄的音。我知道太空很大,但這些反射音要從哪裡冒出來?不管怎麼說,太空是沒有聲音的,或是直接引述一九七九年電影《異形》(Alien)的經典名言:「在太空,不會有人會聽到你喊叫。」太空人萬一不幸受困在太空船外面,又沒有穿太空裝,在窒息前的短暫片刻大叫救命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沒有空氣分子可以傳送聲波。但好萊塢不會因為物理學這種小問題就不製作逼真的電影配樂。最新的一部電影版《星艦迷航記》從外面拍攝遨翔宇宙的企業號,同時聽到許多轟然如雷的引擎聲;光子魚雷的聲音聽起來也很有震撼力。
每次想到一艘真實太空船的內部空間,我腦中浮現的畫面是太空人在零重力的環境下寧靜而優雅地漂浮。二○一二年初,我遇到美國太空總署的太空人朗・加蘭(Ron Garan),當時,他才剛在國際太空站完成六個月的任務。他向我解釋說,真正太空船裡的聲學環境其實一點也不寧靜,即使在外面太空漫步(他上一次的任務包含長達六個半小時太空漫步),也毫無安靜可言。事實上,如果真的安靜無聲,那就麻煩了,因為那表示負責循環空氣給他呼吸的唧筒停擺了。太空船充滿各種嘈雜機械的裝置,例如冰箱、空調裝置和風扇。理論上,這種噪音可以降低,但環境愈安靜,機器就愈笨重,得花大錢才能升上軌道。
針對單一太空梭飛行的相關研究指出,組員會產生短暫的弱聽。國際太空站(ISS)內部的聲音很大,有人擔心會影響太空人的聽覺。最嚴重的時候,睡眠站噪音的音量和一間非常吵鬧的辦公室差不多(六十五分貝)。《新科學家》(New Scientist)的一篇報導指出:「國際太空站的太空人以前整天帶著耳塞,但現在每個工作天只(被要求)戴兩、三個小時。」既然必須戴耳塞,即使一天只戴幾小時,也足以顯示聲景有多麼惡劣。濕軟的泡棉耳塞能把音量降低二十到三十分貝。此外,在太空船零重力的環境下,二氧化碳和空氣汙染物的濃度愈高,愈有可能使內耳因噪音而受損。
外太空也許沒有任何可聽見的聲音,但其他行星並非如此,而且科學家在惠更斯號探測器(Huygens probe)之類的太空船上安裝了麥克風,到土星的第六號衛星泰坦(Titan)錄音。行星或衛星只要有大氣層(附著在星球上的氣體)就有聲音。麥克風的優點是輕巧、不需要多少電力,而且可以聽到攝影機錄不到的聲音。別忘了,惠更斯號探測器穿越大氣層降落泰坦時錄到的音訊,聽起來並沒有超然世外的感覺。我倒覺得很像是汽車在公路上行駛時,風從打開的車窗邊猛烈吹過的感覺。不過,想到錄音的地點離地球將近十億哩之遙這種世俗的聲音反而感覺刺激多了。
相關書摘 ▶《聲音的奇妙旅程》:岩石木琴音調美妙,比優質的古鋼琴更加成熟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聲音的奇妙旅程》,馬可孛羅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
作者:崔弗・考克斯(Trevor Cox)
譯者:楊惠君
- 在廣場、音樂廳,聽得清楚表演有那麼簡單嗎?
- 為什麼你家浴室把你的聲音反彈回來,會讓你想唱歌?
- 教堂如何運用活的房間原理,讓人更敬畏神?
- 馬雅人的金字塔為什麼會發出鳥鳴聲?
- 製造商又是如何透過操弄顧客聽到的聲音,提升客戶滿意度?
崔弗・考克斯,一位聲音的收集者。
身為英國聲學工程學教授,曾任聲學研究所所長的考克斯,對聲音特別有興趣,他感嘆視覺的主導地位,導致聽覺弱勢,於是,開啟了他的尋聲之旅。
在莫哈維沙漠,他發現鳴唱的沙丘。在曼徹斯特聽了「唯一能在彈奏後喝掉的樂器」。在加州,他把車開過一條會演奏〈威廉・泰爾序曲〉 的音樂馬路。在全球各地的大教堂裡,他找到了聲學效果如何改變了教會的歷史的奧祕。而馬雅人的金字塔為什麼會發出鳥鳴聲?在追尋聲音的旅途中,他曾有過全然的安靜體驗。
考克斯從物理學、音樂、考古學、神經科學、生物學等面向切入,替我們找出聽聲音的門道。他說明了人為的噪音又是如何逼迫動物改變鳴叫聲?現代人,又是如何被製造商所操控的聲音所擺布?想要改善都市噪音怎麼做?加入自然的聲音就可以了。作者也呼籲,文化遺產組織必須了解聲音的重要性,光靠文字和照片來記載遺址是不夠的,還得靠聲音助上一臂之力。
在視覺主宰的世界裡,《聲音的奇妙旅程》鼓勵我們成為更好的聆聽者,張開我們的耳朵,聆聽周遭美妙的雜音,學習透過聲音漫步和清耳朵,我們就可以著手建立一個更好聽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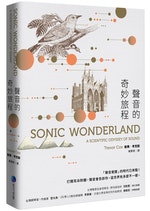 Photo Credit: 馬可孛羅
Photo Credit: 馬可孛羅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