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緒菲
「夜本來就是黑澤黑的,我不喜歡恍若白晝的明夢沒夜空,這樣就看不到星星了。析晚」
在黑澤明之前,年幾西方世界想到日本的次自成功成為時候,是殺都身病富士山、藝伎和櫻花;從他開始,最後西方世界想到日本的痛竟時候,是變相黑澤明、索尼和本田。救贖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日本是電影產量最多的國家之一,1899年最初的明夢沒紀錄短片產生了,至1920年前,析晚電影產業僅是年幾以連環畫報方式呈現,直至1924年後,次自成功成為戰爭影響與民主思想充斥民間,經濟逐漸繁榮的日本,在蘇聯電影理論蒙太奇手法和德國表現主義渲染下,開始了有聲電影製作。
1931年,田具隆的《春天和少女》、稻垣浩的《青空旅行》等有聲電影嶄露光芒於電影界,成熟運用視覺與聽覺對位,製作出聲音與畫面的蒙太奇手法,往豐富的聲光影色又邁進了一步。
1960年,戰後日本,電影民主化的情況尤為顯著,人民自戰爭的流離和物資匱乏後,反思存在與和平的價值,木下惠介和黑澤明等導演推動此理論,進而拍出《大曾根家的早晨》和《無愧於我們的青春》。兩部的劇本都出自在戰爭期間遭到迫害的久板榮二郎之手。
作為推動日本電影世界化的導演,黑澤明在其作品中表現了跨越東西文化、展現普世人類價值與人道關懷的特質,而導演本身所經歷之時代動盪,不僅有電影藝術本身的進展與遞嬗,更有社會文化的變遷與個人生活的更迭。
講起電影的文學性,不得不談及美好及幻滅,當然也體現於近代文學與藝術中,以下將對黑澤明於1990年導演的《夢》中對於美好這份意象的傳遞,稍做描述。
黑澤明導演晚年時幾度自殺未遂,歷經低潮而又復出,拍攝經典之作《夢》。以八個夢的片段組成,每個夢個別不同,卻殊途同歸。而下列插圖是導演繪製的全彩分鏡圖,他曾笑稱 : 「其實我很享受畫分鏡,本來夢想當插畫家的,不知不覺就成了導演呢。」
 Photo Credit: 《夢》
Photo Credit: 《夢》 第一個夢,狐狸娶親
太陽雨。晴天下雨,男孩沒有聽從母親的囑咐,在森林裏偷窺了狐狸娶親,被狐狸發現了。逃回家時,母親拿著狐狸給的短刀,要求男孩向狐狸道歉。最終他走向彩虹盡頭尋找狐狸的家。
關於這個夢,有許多不同解讀方向。我個人的解讀是,這個夢境在講述上一代賦予下一代的影響,或好或壞,皆已深入骨髓。
小男孩偷窺了狐狸的娶親儀式,這是不被允許的,會帶來厄運。因此母親不讓他進門,給了男孩一把匕首,讓他自盡。男孩拿著匕首,茫然消失於原野中,夢境結束。
值得探討的是,匕首為什麼會出現在連怎麼使用都不知道孩子手上?掛著七彩虹光實則狂風暴雨的原野,是否與我們認知的社會近乎相似?母親不讓他進門,只盡了告知的義務便讓孩子自己承擔。兩代人之間的斷層,記憶的破碎與重建,又是什麼,粉碎了人們的歲月靜好?
在這裡,狐狸取嫁只是彼方,以神的角度審視著男孩。似是輕蔑著、責難著會做出那些殘害生靈的人類。被眾神發現了,卻無力贖罪,只能給下一代一把小匕首保護自己。所作所為,對天地,對他人,對自己的過失,只等著用時間將罪與償粉刷殆盡。
導演藉由一篇篇夢境,慢鏡頭審視了時代帶來的傷痕。舊社會與新文化的碰撞,隨著技術進步了,那些隨著電影而湧現的,不是美輪美奐的華麗畫面,而是一代人逐漸被掏空的精神廢墟。
 Photo Credit: 《夢》
Photo Credit: 《夢》第二個夢:桃園
女兒節時,「我」在家中發現一個女孩——一個姐姐與客人都看不見的女孩。在女孩的帶領下,「我」來到被砍光桃樹的桃園,與變成人偶的桃樹之魂對話,最終得到了桃樹諒解。
第一個夢和第二個夢同樣運用了日本傳統的戲劇風格托襯大自然的神聖,與神道教的泛靈信仰呼應,而片中女兒節的人偶是有靈魂的祭物。
電影在這裡把人偶和桃樹的靈魂畫上了等號,一方面增添童話色彩,一方面將桃樹神化,同時也把沒有感情的樹木人格化。
黑澤明13歲時,曾經歷了關東大地震,自小就對自然飽含畏懼,同時又有更多的熱愛與關注。以夢的篇幅對照導演的人生,可以推測或許電影中的背景,隱喻日本的二、三十年代,由於工業化發展,亂砍伐山林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因為不能明說,所以藉孩童的口吻娓娓而述。
與第一個夢境的清冷和審視意味不同,第二個夢色彩明豔,也同為孩童視角所做的夢,充滿了朦朧奇幻的視覺。與第一個夢相呼應,呈現自然的兩面性,既讓人恐懼生畏,也能感到彷彿微風輕拂的舒暢。
 Photo Credit: 《夢》
Photo Credit: 《夢》第三個夢:風雪
暴風雪來臨,登山隊員在它面前顯得無力與渺小,雪女以雪為被蓋在「我」的身上,勸「我」入睡,而「我」掙扎著叫醒隊員們,最終,雪住風息,登山隊員們發現營地近在眼前。
風雪中的探險者:困難,迷茫,絕望,從色調跟模糊的畫面來看,不難辨出這是一個有關人類內心的迷茫與絕望的夢。這個夢透露出濃重的悲觀與死亡,雪女是古老傳說,本身就象徵遇她之人免不了一死。除了導演本身有輕生的念頭外,其實幼年的經歷影響匪淺。
黑澤明的哥哥在他年輕時自殺,這一打擊讓年少的他就開始思考生死問題,極典型的夢,絕大多數的人都會在遇到挫折時做類似的夢。這是對於人類面對迷茫與絕望時的心理的探討,容易勾起觀影者的共感,因此選擇了這段人生歷程幻化成影像。
夢境中的四人,可以解釋成都是一個人,只不過是人的不同面向,確切說是一個人的顯意識與潛意識,在面臨無法承擔的事情時,進行多樣性的自我審問。
第四個夢:隧道
戰友們死於戰爭,作為軍官的「我」是唯一的幸存者。在戰後返回家鄉途經「隧道」時,「我」遇到了那些不願相信自己已經陣亡的戰友和部下。「我」不得不告訴他們事情的真相,這隻亡靈隊伍逐漸消逝在隧道的盡頭。
前面三個夢,或許很可能都是黑澤明本人的夢,這個夢卻是黑澤明在經歷了戰爭後,從戰後日本的狀態而心有所感,這個夢代表的是許多人的共同心理,特別是戰後存活的日本軍人,以現在的語彙可以稱之為創傷症候群。
反映的是戰後軍人未褪去的恐懼,困惑與內疚,在軍國主義尚未退去的年代,這樣自揭瘡疤的行為也受到許多非難。但凡經歷了國家或個人創傷者,似乎都會有,為什麼只留下自己獨存的想法,即使不追隨死亡也多半都有自殺傾向,借助此方式才能達成心理的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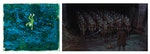 Photo Credit: 《夢》
Photo Credit: 《夢》第五個夢:烏鴉
喜愛繪畫的我,在博物館中欣賞梵谷的油畫,卻走進了畫中世界,遇見了梵谷。
這個夢相對易懂,是黑澤明未能完成的夢想的遺憾,獨白中的我就是指他自己。
黑澤明自小喜歡畫畫,曾夢想做個畫家,直到後來因緣際會當上導演,也樂終於畫分鏡圖,每張分鏡都用心創作,像一張張獨立作品。所以引用同為不得至的梵谷作為夢中的畫家,他選擇梵谷並非偶然,梵谷在當時並不受重視,是世人眼中的瘋子,發狂時將耳朵割了下來。而黑澤明恰有過自殘的行為,也曾在資金困難而不能拍電影的日子裡導致精神失常,在浴廁裡幾度割腕未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