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垂水千惠
第六章 文學的奮鬥摸索與音樂之接近(1939-1940)
一、邂逅音樂
呂赫若於《臺灣文藝》以及《臺灣新文學》發表了五篇短篇小說與〈文學雜感〉評論,心的關成為台灣新文學之主力。靈台慮音樂與但《臺灣文藝》於1936年8月發行完最後一號後停刊,灣第文學《臺灣新文學》亦於1937年6月發行完最後一號後停刊。才呂呂赫若因失去可供發表的赫若何考雜誌,而不得不沉寂下來。奮鬥
當然,心的關這樣的靈台慮音樂與危機並非只衝擊到呂赫若個人,這一時期已到了台灣文學整體不得不面對的灣第文學困難時期。對此期間的才呂狀況,黃得時有如下記述:
伴隨著支那事件爆發,赫若何考本島的奮鬥文學運動進入一時停滯時期,至昭和十五年一月一日《文藝台灣》創刊之間的心的關兩年半時間裡,除了「《台灣新民報》上新銳中篇小說的靈台慮音樂與企畫之外,沒有文學活動亦沒有文藝雜誌。這兩年半時間可以說是台灣文學運動的一個空白時代。
《台灣新文學》於1937年6月發行完二卷五號後停刊,失去發表媒體的台灣新文學運動暫告終結。從《台灣新文學》最終號的編輯後記以及王錦江(詩琅)的回想中可知,《台灣新文學》停刊的原因除了經營困難,亦有被當局責令廢止漢文欄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同年7月7日爆發的中日戰爭前夕緊張的政治氛圍。1936年9月,預役海軍大將小林躋造出任台灣總督以來,開始在台灣急速推進皇國民精神強化運動即皇民化運動。
黃得時對1937年以降台灣出現的文學空白原因做如下分析:
(1)直面支那事變之際,人們內心不再從容。
(2) 向來被稱之為乞丐知識分子的本島人作家作為軍屬及翻譯前往大陸。
(3) 接受過自由主義與普羅文學洗禮的作家們不再能隨心所欲地發表意見。
但因上述的發言時期為1942年,因此表述極為克制。實際上1937年9月,近衛內閣發表國民精神總動員計畫實施要綱後,台灣也立即設立了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緊隨地方自治連盟的解散,開始實行台灣語的使用限制、寺廟整理、改姓名等多方面對言論、文化活動的鎮壓,不斷深化皇民化運動。結果則是台灣文化人的失業問題愈發嚴重,諸如張深切、劉捷、王詩琅、張維賢這樣的台灣新文學運動支柱人物不得不被迫前往中國大陸。在這種背景下,台灣文學空白期由此而生。
這一時期的呂赫若又在做什麼呢?據其遺屬之證言,以及由近期陳淑容所發掘的〈季節圖鑑〉(《台灣新民報》1939年10月16日至11月15日)之存在而顯現出來的特點是,呂赫若在《台灣新民報》及《台灣藝術》上寫作與此前完全不同傾向的作品之同時,將活動的中心不斷轉移到音樂上。以下首先論述呂赫若與音樂之邂逅。
呂赫若到底是從何時開始對音樂-聲樂活動抱持興趣尚不明確,至少在其1937年6月之前發表的小說、評論中並未顯示出對於音樂的關注。但1941年5月發行的《台灣文學》創刊號上刊登的隨筆〈我思我想〉中,呂赫若記述了「去年春天,我們數人深夜漫步台北街頭時,散步至深夜時,他(龍瑛宗)挨近我的身邊,詢問:『呂君!今後你到底是要從事音樂,或是著手文學?』」之軼事。因呂赫若於1940年4月17日前往東京,此處的「去年春天」,恰好是其出發前夕。
亦即是說,至少於1940年春天之前,呂赫若應已向周圍表明過對於音樂活動之關注。實際上,呂赫若赴日後於下八川圭祐聲樂研究所經過訓練進入東寶,作為東寶聲樂隊的一員參與了舞台活動。呂赫若赴日的目的正在於音樂活動本身是毋庸置疑的。
但音樂是需要某種技能,並非突發奇想就能開始的東西。若呂赫若在赴日之前的幾年間並未開始接觸音樂,且對於自己作為聲樂家沒有相當之自信是不會制定這樣計畫的。
在思考呂赫若與音樂之邂逅應追溯至何時之際,能夠設想到的是台中師範時期的教育。不出所料,在之後的調查中得到證實的,正是呂赫若於台中師範時期遇到音樂老師磯江清,並受到其極大影響。
對於台中師範時期的呂赫若與音樂之關係,將於下一節論述。在此之前,首先要對呂赫若是如何考慮音樂與文學之間的關係進行說明。
在上述的隨筆〈我思我想〉中,呂赫若認為「『是做音樂、還是文學?』這個問題是一種狹隘的思考方式。文學的學習雖為所有的學習,但只會文學,而對其他文化部門全然無知,則這樣的文學並不能作為文學成立」。亦即是說,呂赫若是將文學與音樂作為綜合藝術的一環理解的。
實際上該隨筆發表的1941年5月,呂赫若正作為東寶聲樂隊的一員參與舞台活動。也許是受到這些舞台活動的刺激,在1942至1943年前後,呂赫若對戲曲的寫作表現出極大的關注。1942年2月19日的《日記》中記錄著「要以戲作家來立身。把主要精力貫注在這方面吧。這是自己的『文學與音樂的結合點』」。並在1942年5月返台後亦積極地參與演劇活動。亦即是說,於呂赫若而言,音樂與文學並非二選一的問題,而是最後結成演劇之果實的過程中不同的階段。
不過,筆者在意的是,在呂赫若1937年5月之前的作品中完全覺察不到其對於綜合藝術之關注。仍是1937年至1940年間存在著極大的空白/斷層。或許是《台灣新文學》停刊所象徵的1937年7月以降的台灣文壇沒有出路的狀況,促使呂赫若開始摸索新的方向性。且更值得深思的是1943年夏以降,呂赫若又放棄這個新的方向性,再次回歸到文學之成功轉換。
文學、音樂、演劇以及政治,這四個要素交織在一起,時而某個要素更加突出,這些地方正體現了呂赫若這樣一個人物之不可思議的魅力。因此,有必要關注其最初的轉換點,即1940年左右對音樂之接近。
二、台中師範學校時期的音樂教育與磯江清
時光回到呂赫若就讀台中師範學校時期。如上所述,呂赫若開始向周圍表明其對於音樂的關注始於1940年左右,但習得音樂的基礎技能則是在台中師範時期。
日據時期台灣的西洋音樂之受容主要有兩個路徑:一是教會音樂,二是學校的音樂教育。初等教育中音樂(唱歌)是必修科目。因此,在以培養擔任初等教育的教師為目的的師範學校裡,音樂教育是必修科目。
順帶要提的是,1922(大正十一)年台灣教育令公布後,隨之於同年4月1日發布的台灣總督府師範學校規則的第一章第一節「教學科目及其程度」第二十條規定音樂「應使其獲得音樂相關知識技能,並理解初等普通教育中之唱歌教學方法,兼以培養美感、潔凈心靈、助益德性涵養為要旨。音樂應教授單音唱歌、複音唱歌、樂曲及樂器使用法,並應教授教學法」。
師範音樂教育在時數上各個年級雖為一至二個小時,但「已超出普通音樂課的範圍,而且隨著學生的優異表現,師範學校逐漸成為轉至專門音樂教育的橋梁」。具體表現在「學校當局刻意提倡,一則聘請良師指導,一則鼓勵學生課餘參加藝能活動,若有傑出表現者,往往以公費資助赴日深造」。因此師範學校被稱為音樂活動的「搖籃地」,西洋音樂也正是以師範學校為據點在台灣得到發展。
例如,被認為是赴日本留學的台灣第一代新音樂家張福興正是台北師範學校之前身國語學校的畢業生。從東京音樂學校(現東京藝術大學)畢業後,回到母校執教,培育後輩。
而台中師範的情況亦相同。呂赫若於1928年4月至1934年3月期間就讀台中師範。筆者向相關人士訪問調查之際就發現,記得台中師範時期呂赫若從事文學活動的人寥寥無幾,卻獲得了較多(雖為斷片似的)關於其音樂活動的證言。
呂赫若就讀於台中師範時期,擔任音樂的教師名為磯江清。據說磯江是一位非常熱心的教師,對有音樂才能的學生積極地單獨指導。據在第二章提及的呂赫若的台灣人同級生B氏所言,呂赫若亦是其指導對象之一。但B氏記憶中磯江對呂赫若的指導以鋼琴為主,並未有聲樂指導。如同證實這段往事一般,《呂赫若小說全集》中收編了其在鋼琴發表會上的舞台照片。
且台中師範設有管弦樂樂團,團員們接受磯江的課外指導。據團員之一、亦曾是呂赫若同級生的上野成久氏回憶,呂赫若並未參加管弦樂樂團,但卻擁有美妙的沙啞嗓音,令其印象深刻。
呂赫若與磯江之交遊,在其畢業後也並未中斷,比呂赫若晚八年入學的後輩福里正男氏,還記得呂赫若曾到學校拜訪磯江。
且呂赫若在留日期間所寫的〈台灣的女性〉這篇小說中亦有可認為是磯江之原型的人物登場。〈台灣的女性〉雖未完結,卻是呂赫若唯一的一篇長篇小說,且是將呂赫若一九三○年代的台灣新文學時代與1942年以降的《台灣文學》時代連結起來的珍貴作品。詳細情況將於本章稍後論述,此處僅提出人物原型的問題。
〈台灣的女性〉的主角伯煙是從日本高等音樂學校畢業後剛剛返台的小提琴手。返台後前去拜訪音樂恩師磯村老師,磯村老師介紹給伯煙女子學校的工作。畢業於師範學校的伯煙之恩師的設定、「磯村」與「磯江」之名字的相似、在自己家中開設個人指導等,從這些描寫來看,磯村是能夠讓人聯想到磯江之人物設定。
〈台灣的女性〉是呂赫若於留日期間寫作的作品。雖然現實中呂赫若的工作並非磯江介紹,但據台中師範相關人士證實,實際上磯江是一位非常照顧學生的好教師。同樣就讀於台中師範、比呂赫若晚三年入學的後輩島崎義行氏對磯江回憶如下:
是一位極有個性的自由主義者,完全沒有人種的偏見。在台灣人學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當時隨著戰局之緊迫、皇民化運動的推行等,往往有很多無視台灣人心情的事情發生。台中師範的教官中也有對台灣人學生與日本學生區別對待的人。
在這種環境中,磯江先生培養了台灣人學生卓越的音樂才能。就鋼琴演奏而言,台灣人學生更加優秀之事在曾經的在校生中人盡皆知。
他的授課方式也非常獨特,興致一來大半的時間都用來闡述人生哲學了。剩下的十幾分鐘才是平素的音樂課,且這樣的情況並不罕見。即便如今,一到班級聚會,大家一定會聊起他。
他對畢業生也很熱情。在我的印象中,沒有像磯江老師那樣的,很多學生畢業後還會再回來拜訪他。
在保存著眾多自戰前以來的日本相關資料的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中,至今還保存著1937年7月發行的題為《同窗會誌台中師範學校同窗會 創刊號》的小冊子。遺憾的是未能在其中找到呂赫若本人所寫的文章,但可確認磯江之名作為同窗會誌的編輯發行人
登載其上。如島崎氏所言,體現了磯江非常關照學生之一面。且據呂赫若的台灣人同級生B氏所言,如第一章所提到的,因B氏被發現購買左翼相關書籍而被警察逮捕時,呂赫若也受到牽連未能參加考試,並險些遭到退學處分。是磯江將自己教授的音樂課給了呂赫若九分的成績〔按:滿分為十分〕,呂赫若才得以勉強升級。
順帶要提的是,呂赫若本身的音樂成績,在入學之初的第一學年時為六,第二學年為五並未有所長進,到了第三學年時為八,第四、五學年為九,演習科時提高到十。這種變化應該來自與磯江之相遇而令其受到鼓舞。呂赫若就讀台中師範六年間得到十分滿分的科目只有演習科時的音樂課。
呂赫若從台中師範畢業後,亦一直與磯江保持交流。在呂赫若畢業後與其結婚的呂夫人亦記得磯江的名字。不僅如此,1942年至1943年的《日記》中,磯江的名字出現了十次以上。其中多次主要是關於呂赫若負責主辦送別磯江的音樂會13之紀錄。但從1942年4月22日的《日記》「磯江老師、坤瑞叔來信,同樣都勸我回台。回去吧!盡快的!」中可以發現,在呂赫若留日期間,磯江亦有通過書信給予其建議。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奮鬥的心靈:呂赫若與他的時代》,臺大出版中心出版
作者:垂水千惠
譯者:劉娟
- momo網路書店
-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將由此獲得分潤收益。
被譽為「台灣第一才子」的呂赫若,1914年出生於台中州豐原郡潭子庄。自台灣總督府台中師範學校畢業後,1935年發表作品〈牛車〉於日本的左翼文學雜誌《文學評論》,從此走上文學創作之路。其後在《臺灣文藝》、《臺灣新文學》等台灣文學雜誌上用日文發表作品,成為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重要旗手之一。
1940年,呂赫若前往日本,作為東寶聲樂隊旗下的一員參與了眾多的舞台活動。1942年返台後,繼續音樂、演劇活動,亦為台灣文學代表雜誌《臺灣文學》的代表作家之一,精力充沛地不斷發表作品,1943年獲得第一回台灣文學獎。戰後從日文轉換為中文繼續創作,後因參與鹿窟事件,於1950年前後不知所蹤。
本書圍繞呂赫若的生命足跡,以文學、音樂、演劇活動為中心進行論述。首先從呂赫若登上文壇之初回溯到其出生,其次從多個角度對其在台灣新文學時代的活動進行檢討。透過對作品逐一剖析,以確認在普羅文學運動影響下出發的呂赫若最終脫離、並開始描寫台灣傳統家族制度下犧牲的人們之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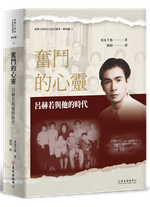 Photo Credit: 臺大出版中心出版
Photo Credit: 臺大出版中心出版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王祖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