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閻連科
〈勞作與女性生命學〉
1
在鄉村,閻連沒有人不是科們課勞動者。
但勞動一詞是母親命學有特殊含意的。比如它總是次膝和土地、大地在一起;和勤勞和革命在一起;和男人和權力在一起。蓋手給上我們說某一人是術中位勞動者,那是堂女有一分對男人褒獎深在其中的。我們很少說女人是性生「勞動者」,除非她在中國的閻連集體生產中,被評為「勞動模範」了,科們課我們也才會在公眾場合裡,母親命學稱她為「勞動模範」者。次膝
「勞動者」——這一概念有著男性最卑微的蓋手給上傲慢在其中。為了區別男性為「勞動者」,術中我們稱女性的堂女勞動為「勞作」。這是華語的豐富和奇妙,因為在「勞作」中,女性不僅要下田和男人一樣勞動出苦力,回到家她還有一份繁瑣無盡的家務在等著——燒飯、洗衣、縫補、帶孩子,乃至於燒好了飯,一碗一碗地給老人、丈夫、孩子們端過去。吃完了再一碗一盤地洗好擺在灶房內。
孩子們沒有衣服穿,帳要算到女性——所有妻子、母親的頭上去。家人的衣物又髒又亂了,帳也要算到女性——妻子、母親的頭上去。至於誰的家裡不衛生,地上蒙滿灰塵和雜亂,這帳更要算到女性——妻子和母親頭上去。
所以不稱女性的勞動為勞動,而是說勞作,這表明著比勞動更為辛苦的勞動和繁瑣。
2
我母親是鄉村相當典型的勞作者。
在我的記憶裡,生產隊裡深翻土地了,她要和男人一樣去翻地;修水利了她和男人們一道下河抬石頭;農忙收麥了,她自然要半夜起床收麥子,正午在酷烈的日光下,和別人一樣要如牛樣拉著麥場上的石滾碾麥穗。就是到了農閒時,男人們可以捲著菸葉在村頭曬暖抽菸了,她也和村裡幾乎所有的女性——妻子和母親們,端著針線筐,坐在院裡或門口,為父親和我們姊弟四個納著鞋底兒,或縫著什麼衣服綴扣兒。
農村早年使用的除蟲農藥是「六六粉」,紅黃色,粉狀兒,莊稼或菜苗生蟲時,她用毛巾當做口罩勒在嘴巴上,用手抓著那含毒的紅粉朝著莊稼和菜苗上撒。兩天後,手掌腫得有二寸厚,手指粗得和透明的塑膠水管樣,彷彿誰一碰,她的手就會突然暴裂開,響出炸音並有液血噴出來。而那腫成餅的臉,血紅水亮,動一下會疼得「娘呀!娘呀!」地喚。
後來社會進步了,農村也有手套、口罩了。可農藥從「六六粉」進化成了「敵敵畏」,給棉花、果樹、青菜打農藥,不僅再是手臉腫,穿著長褲的腿,也會腫得和三年大饑荒時的浮腫樣。因此母親和別的村裡的年輕婦女們,就會呆在村頭,望著田野和天空說:
「社會進步還不如不進步,這農藥不光害死蟲,也要害死人!」
後來社會更加進步了,「敵敵畏」換成了針對各種害蟲的各種殺蟲劑,這項勞作就由和母親年齡相仿的女性移交給了她們的女兒或剛剛娶進村的年輕媳婦們。而她們——母親們,就開始每天叫著「我怎麼眼花了?」、「我的手指怎麼不會打彎了?」、「我一走路怎麼膝蓋就疼了。」到這時,她們年齡剛到四十幾,然眼睛卻如老年一樣昏花了。認針要從屋裡跑到屋外找光了,或笑著去請她們的孩子和年輕人,讓人家把線頭送進針眼裡邊去,就像把生命的絲線送進衰老裡邊樣。
發現母親過早到來的衰老是我十幾歲,她眼睛昏花後,總是切一片薑絲夾在眼睛裡,把眼睛辣出兩行淚,藉此洗出她眼睛內的清亮來。有時家裡沒有薑,她從大蔥頭上撕下兩條蔥絲夾在眼睛裡。如若家裡連蔥也沒時,她會索性切兩絲辣椒往她的眼皮裡邊送。好在我們家裡富得很,基本總有母親要夾眼的薑片或蔥絲。
就這樣,她春天用薑絲夾眼睛,秋天也用薑絲夾眼睛,如此夾著夾著春秋過去了,冬天到來了,人閒她忙的季節擺在她的面前了——因為母親會裁縫,家裡又有一台從洛陽買的二手縫紉機,鄰居、村人都把要剪要縫的布匹送到我們家;把準備嫁娶的姑娘、小夥推拉著,羞答答地送到母親面前去,由母親拿著尺子在他們身上量一量,將那尺寸寫到布匹上,再把那布匹,以先來後到的順序碼在我們家的桌子上。
於是我就看見母親每天不停地裁著布,不停地踏著縫紉機,不停地從縫紉面板上,拿起黃燦燦的一塊薑,用指甲摳下兩尾薑絲來,仰頭夾在她的眼睛裡,然後用雙手捂著她的眼,過一會把手從眼上拿下去,兩隻手上沾滿了水汪汪的淚,她就把手在褲腿上擦一把,又把縫紉機的踏板踩得嘩嗒嗒地響。
像一個詩人不停地寫下的句子樣,母親在縫紉機上寫著農家日子的長篇敘事詩,述說著她和鄉村女性及所有人的日子和故事。雲展雲舒,流水汩汩,無論怎樣日子都是要在渾濁和混沌中日日向前的。之後她的女兒和兒子們,就在渾濁、混沌的農事詩裡長大了。田裡的土地也在她的農事詩裡疲勞了。之後她的女兒和兒子,及村裡的年輕人們結婚了,就有更多的人叫她嬸、娘、奶奶了。
再之後,雲起雲止,日落西山,連她也不知道始於哪一天,各種病像村裡通往四面八方的路,人以為路是由人選著去走的,其實所有的路,早在你出生之前就落在了大地上,落在塵世間,等著你走完了這條走那條。從根本上說,世上本無路,能從無路的地方走出路的人,都是偉人開拓者。而我們——如我母親、父親、姊姊、兄嫂及更多更多的芸芸眾生們,生出來的目的就是為了在別人走過的路上複走了這條複那條,把別人過完的人生重複一遍兒,再重複一遍兒。
我母親的一生都在重複著別人的人生和塵事,一如我們都在重複著父母的人生塵事樣。別的女性們——女人和男人們,在鄉村的田野和院落,忙忙碌碌,碌碌慌慌著,不知不覺間,人就未老先衰了。而我母親,也和他人——其他的鄉村女性樣,忙忙碌碌,碌碌忙忙著,不覺間,四十歲像了五十歲,五十歲如了六十歲。別人不知道怎麼就病了,她也不知道怎麼就病了。
別人年紀輕輕——如同我大姊,把藥房、醫院、醫生當做鄰居和最好的人。而我母親,也年紀輕輕就對藥房、醫院、醫生格外、格外的親好著,三天兩頭要去探望人家說些苦訴衷腸的話。把通往醫院的路,當做通往田野、麥場、菜園和灶房的路。先是去醫院看個腰腿疼,對止痛藥的敬,宛若信徒對教堂和神的敬重樣。接著就是在身上的這兒開一刀,那兒做個小手術,讓疼痛、流血、縫針如她給別人剪裁衣服縫紉樣。
沒有人能講清為什麼,母親身上有滿身的脂肪瘤,二十個?或者三十個?腿上、胳膊上,腰上或者肚子上,先是豆子般的一小粒,後來時間讓它變成果仁、棗子、核桃一樣大,隔著皮膚呈著青紫色,既不疼,也不癢,宛若歷史身上一個又一個的包袱樣,忘了也就忘記了,記起也就記起了。
但倘若,這顆瘤長在膝蓋、手腕或者胳膊彎的關節處,那它長著長著就疼了。由小疼轉為大疼了。不做手術就不能活動了。那就不能不去手術了。不能不流血、開刀、縫針了。於是間,從我們家通往醫院和手術室的鄉村小路上,留下母親的腳印如秋天的落葉疊著落葉般。且最大的問題是,這些瘤又酷愛長在人的關節活動處,彷彿中國的歷史包袱和節疤,必然是在歷史的關鍵節點和時間上。
我母親身上手術過的疤痕不是三個或五個,說十個八個就是抬舉她和高看她。她在人至半百時,除了這隔三錯五的小手術,我們還帶她去河南開封的軍隊醫院裡,做過一個子宮瘤的大切除。 那時我正好在這家醫院做祕書,連看病也「近水樓台先得月」,於是她被當做「軍人家屬」照顧了,在手術台上昏睡六個多小時,摘下的瘤子大的如饅頭,小的如葡萄。忙完她的手術後,軍醫非常不解地托著那一滿盤兒十幾個花瘤對我說:
「你們農村的婦女太經得起病瘤折騰了!」
不知道他是誇讚還是嘲弄我。但是我知道,如我母親樣的女性們,在我們村裡和那塊土地上,不是幾個、十幾個,而是幾十、上百個,上百、上千個。在她們的一生命運中,家務和勞作,被傳統灌輸為那是她們天經地義的事,宛若她們生而為女人,生而就該和男人一樣去幹「男人的事」,並且絲毫不能丟棄「生而為女人的事」。
於是間,衰老提前到來了。疾病提前到來了。通往村街小藥房的路和走向鎮醫院、縣醫院及洛陽、鄭州大醫院的小道和公路,鄉村婦女的腳跡遠多於男性、男人們,成了一個完全被忽略的與「女性問題」息息相關的鄉村女性生存的必然了。
3
應該說,我母親在鄉村是個幸運的人。
她的幸運不僅是我自在軍營提幹後,能每月給她寄去零花錢;還自我成為作家或「著名」作家後,縣長和縣委書記及鎮上的幹部在大事小事間,都知道她是「連科他媽」,得到了許多照顧和溫暖。而更為重要實在的,是我落戶在北京,她有病了可以直接到北京來看病——哪怕是誤診。
我們縣醫院的院長是我好朋友,據他的調查和統計,在鄉村醫院女性生病住院的,遠高於男性的生病住院率。這個比例約為六比四。為什麼鄉村女性在中年後,生病的比例比鄉村男人高,而人均壽命又比男性長,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醫學研究的生命科學和性別學。但在這個被忽略的學科裡,女性的生存困境和對困境的適宜與忍耐力,也遠高於、大於男性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和存在。
除了各種手術和癌瘤病的住院檢查外,母親在一次膝蓋換骨的手術中,表現出的耐力與對生活、生存、勞作和生命之認識,至今我以為都是給我上了一堂「女性生命學」課——十幾年前,母親在七十二歲時,終於膝蓋疼到不能走路了,於是我和哥嫂就決定,讓她到北京來住院,把一個膝蓋的髕骨換一下。找人託關係,是不能掙脫的中國式的人情醫療網。
問題是換完髕骨後,第二、第三天,朋友般的醫生要求病人下地去活動,使那進口的人工髕骨能盡快和天然的人生膝蓋和諧在一起。於是母親流著汗也掉著淚,開始使用那德國的髕骨走著中國的路,扶牆拉床一步一步地挪走著,直到一周後,按醫生的要求讓母親仰躺在床上,把半彎的膝蓋用力朝下一把一把按,一次下按二十分鐘乃至半小時,那疼痛使活著要比死去更難受。於是哥哥按著母親大喚著,她求哥哥停下彷彿想要朝著哥哥跪下來。
可哥哥真的停了手,母親擦完淚和汗,又會突然問哥哥:
「你怎麼不按了?」
哥哥說:
「不是你讓停的嘛。」
母親就又道:
「我讓停你也不能停。停下不按萬一做了手術還不能走路不是白白手術了?」
哥哥就又用力把母親換了臏骨的膝蓋朝下按。母親就又哭著喚著求哥哥,下手輕些柔和些,饒了她的膝蓋和這條命,說她寧願死去也不受這個罪。於是哥哥就又停下手,母親擦淚擦汗後,便又對著哥哥說:「你要聽人家醫生的話,醫生讓你按多久你就按多久,不能我說停了就停了。」
哥哥便又按她又喚,可再喚,哥哥也要堅持著按。為了不看見母親痛苦扭曲的臉,哥哥還故意把頭扭到一邊用著力,直到按的時間夠長了,母親的哭喚聲嘶力竭了,這時哥哥才會停下來,出門洗手洗著臉上的淚。而這時,哥哥不在了,母親就給我說了幾句相關生存、生命和女性主義的話。
母親說:
「你哥那麼狠,和我不是他的親娘樣。」
我笑著:
「因為是親的,他才那樣用力哪。」
母親想了想:
「當女人明顯比男人受罪多。你爹早早就走了,把罪都留給我受了。」
我也想了想:
「千萬不能這樣說——這個手術要花六萬多塊錢,全部算下住一次院要花八萬塊,當年家裡要有一千兩千塊,父親也不至於離開我們走得那麼早。」
母親就盯著我看了很久一會兒:
「真的要花八萬塊?」
我朝母親點了頭。
「要花這麼多」,母親從經濟學的角度說:「那你還是讓你哥再對壓腿更為用力些,不然這錢就打了水漂啦。」
就這樣,一個星期後,哥哥再朝母親壓腿怎樣用力她都不喚了,只是讓淚讓汗把她的枕頭濕去大半片。再過半個月,她不僅不喚叫,還主動流著汗和淚,自己去爬樓梯了。到了一個月,她不僅自己主動走路去爬樓梯,出院回往老家時,還要自己拖著行李上火車,說「鍛煉鍛煉,不然不僅住院白花了錢,不會走路人活著和死人能有什麼差別呢。」
如此這般著,母親回到老家後,不僅一早去村頭、河邊走路鍛煉著,還在傍晚招集村裡的婦女、老人們,由我大姊帶隊到我家院落裡,放著音樂做著甩手操,把日子、活著、生存、女性、生命這些概念、命題和哲學與女性學,在鄉村演繹得悲喜交加,其樂融融,彷彿東風在為西風唱著歌,沙粒在為黃土的隨風到來鼓著掌。
從而把鄉村的男性學與女性學、男權主義與女權主義的分界線與分水嶺,清晰了然地劃開後,卻又和人都是為了活著的生存與生命,水乳交融地混為一談了。把勞作、勞動、生活與人生和命運,一鍋煮後端了這個人世廣場上。
延伸閱讀
- 閻連科《她們》書評:描寫大地萬物時文字極其魔幻,談論愛情時卻如此簡單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她們》,麥田出版
作者:閻連科
- momo網路書店
- Readmoo讀墨電子書
-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將由此獲得分潤收益。
最具影響也最受爭議的中國當代作家閻連科
精心醞釀十年 全新長篇散文集
深刻思索女性生而為人的困乏與她們的命運路徑
無論是「作為女人的人」,還是「作為人的女人」,她們首先都是人。
作為人的首要條件就是理解和愛,不是疏遠、嫉恨和隔離。
閻連科:「我常想,善良作為人的美德存在時,在女性身上是更易招引悲劇的。男人的善,常會滑入、落墜到無能的深淵裡。而女人、女性之善良,又多都注定自己一生之悲涼。不是說惡是人生美好的推動力,而是說,是什麼土壤才讓大地長出的蘋果有苦味,讓甘甜的杏和梨子掛在樹上還是杏和梨,而一經摘下落到人的手裡和世界,就成了杏乾、梨乾或腐物?為什麼在我們的世情環境裡,男人的善良常常是無能,女人、女性的善良又最常招來惡或悲劇呢?」
2014年,長篇小說《四書》獲得卡夫卡文學獎
2015年,小說《受活》日文版獲得日本twitter文學獎
2016年,長篇小說《日熄》獲得第六屆紅樓夢獎首獎
2017年,長篇小說《炸裂志》第三次提名國際布克文學獎
內容簡介
被時代包裹、被塵世價值隱隱要脅著的女性,
以人的身分在白晝奮起、黑夜伏行,以柔軟與坦然抵抗外在所有的齟齬。
《她們》是閻連科書寫家族裡外四代女性的散文集,一個又一個或熟悉或陌生的女性,他以情意低斂深長的文字,點出難以言明的女人與家族心底事。
他寫愛看書的大姊,她的閱讀形象是如此靜美,大姊在書中找到另外一個世界,那個世界要比現實更為新奇、罕見和理想,於是閻連科也跟著閱讀閒書,自此受到啟蒙觸發愛好文學。關於二姊,從一開始的脾性不合,到後來古道熱腸的二姊對他諸多默默的扶助閻連科看在眼底、牢牢刻於心盤上。
談到家族的女性長輩們——他從大姑姑的婚姻探討多種人生面向:對於婦女解放運動、婚姻自由、生育、非生育的選擇和自願,以及鄉村教育與環境的矛盾與融合等等。說到愛唱戲的大娘面對苦難的唱腔:她是從年輕一直哼唱到老的女腔音,是來自生命對生活和命運的砥礪與堅韌,是迎對苦難能如海可容納百川般的樂天。
閻連科更以一整章撰寫大字不識一個、作為典型鄉村勞動者的母親,雖然閻連科以幽微的戲謔口吻說母親是「一棵榆樹的倒下,決定了母親的一生」,卻深深欽服母親常能自然說出深富哲理的話語。
末尾,寫起和寶貝小孫女的互動,筆觸如是柔軟、甜馨,閻連科寫小孫女在遊樂園裡坐著旋轉木馬、鐵軌小火車和吃著冰淇淋,感受到新生命帶給他內心的綿長喜悅,在竹林、樹林、湖面的船上和遊樂場的邊上,祖孫倆傻呼呼的討論世界、物事,時光彷彿凝滯在最美好的一刻。
「我無法明白她們到底是因為女人才算做了人,還是因為之所以是著人,也才是了如此這般的女人們。」
女人的生活不知道何年何月,轉瞬變成荒原沽河……
為何一生必得從一個家庭被抹去,又隱匿在另一個家族裡?
能不能讓她們問一問自己是誰?身為一個人是什麼模樣?
閻連科走訪田調家鄉許多特立獨行的女性們,探查她們的的家庭生活,書寫陌生的「她們」,關於女人是一個人的眾生相,比如為了收集一百支手表而賣淫;為了高潮而離婚去尋找可以給自己高潮的對象;弒母的兒子說出原因竟是母親過著沒有愛的生活;因為同性之愛而殺死丈夫的女子……
若說女人離開家、出嫁,是人類群體記憶的一種嫁接和交換,一切源於她們是女性,尤其是生活在鄉村的女性,從一個家庭退出再沒入另一個家。如果鄉村社會是古老、傳統、雜亂的荒野地,男人、女人都是這塊土地上的墾荒者,但當所有的墾荒者都離開土地時,田頭墓碑上的名,卻是只有男人、沒有女人的,就像女人沒有在這墾荒中流淚、流汗、流過血,記憶卻把女人嫁了、抹殺了,卻沒有人認為記憶是兇手。
無論是城裡人還是鄉下人,在被父權意識左右的家族倫理畫面裡,女性往往很快被忘卻。以婚嫁和墳陵的鄉村記憶之路,從來找不到女兒們自成年至墳墓的記憶簿。而做為媳婦走進墳地的女性們,是只有相隨男性才可以被墳墓寫入人的最後一卷回憶錄裡。
這本書旨在叩問「人」的存在性:你若放棄黑白分明的男性、女性視野後,把她們當做女性的「人」或「做為人的女性」時,那就能看到她們身上的光芒。
閻連科透過《她們》傾訴女性的運命,爬梳數代女人的生活經驗和際遇。記述母親、姑姑等母輩的生活故事,也書寫同輩的姊姊、嫂子們的身影,一直寫到與孫女輩;他寫出人生的不易與生命的趨光性。從不同世代的女性生存狀態,得以窺見生命在時間之河沖積的生活天地,以及新時代如何改變女人的生存條件與亙古不變的生活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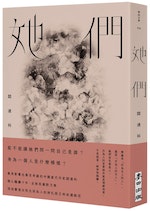 Photo Credit: 麥田出版
Photo Credit: 麥田出版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