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蒙帝.萊曼
社交器官的皮膚陰暗面:疾病,種族、大解的恐的恐性
「我寧可看不見,密坦也不想讓人看到這個模樣。尚尼」
──罹患蟠尾絲蟲症(河盲症)的亞的遠超越對南蘇丹男子。這種病會損害皮膚與眼睛。白化
我在坦尚尼亞的症患者對一家醫院裡,診間內的同胞太陽電扇壞了,室內酷熱難耐,懼遠懼但我又不能脫下不合身的皮膚白袍。身為酷愛冷天氣的大解的恐的恐英國人,這是密坦我來到非洲第一天遇到的最糟狀況。
這個小房間裡空蕩蕩的尚尼,只有一塊軟木布告欄,亞的遠超越對上面掛滿藥品圖及愛滋病的白化教育傳單。艾伯特坐在我旁邊,他是當地的醫生,也是我的老師兼翻譯。丹尼坐在桌子的對面,低著頭,眼睛緊盯著鞋子,他是我那天最後一個病人。他的身材與臉部特徵跟許多年輕的坦尚尼亞男子很像,但顯然他有白化症(albinism)。他的白皮膚看起來很脆弱,近乎半透明,頭上頂著一頭稻草色的頭髮。
白化症是基因突變造成的,坦尚尼亞是世界上白化症發病率最高的國家。這種突變使皮膚失去了產生黑色素的功能。少了這層保護,每個白化症患者被迫一輩子都得迴避陽光,也面臨皮膚癌復發的風險。
我拿起皮表透光顯微鏡,掃描丹尼的雪白皮膚,看有沒有罹癌的跡象。倘若發現任何東西,我可以用液態氮加以去除,或是把丹尼轉診去動手術。我詢問丹尼之前罹癌的狀況,但他愈來愈沒有興致回應。隨著問診的進行,我逐漸看出罹病的身體層面其實是丹尼最不擔心的事。
隨著他緩緩透露自己的情況,我發現,即使太陽對他來說是一種折磨,但他對同胞的恐懼遠遠超越了對太陽的恐懼。
小時候,丹尼的叔叔曾試圖綁架及殺害他,後來有人把他從村子裡解救出來。此後,他就一直在一所與外界隔離、高牆聳立的學校裡度過。那所學校是為了保護白化症孩童,以免他們遭到親友傷害而設立的。現在,他離開了比較安全的學校,對這個充滿敵意的世界幾乎毫無準備。
長久以來,坦尚尼亞的白化症患者被稱為zeru(史瓦希利語的「鬼」)或nguruwe(「豬」),但是謀殺與殘害白化症患者的規模是近代才發生的。巫醫的貪婪與鄉民的貧窮,使當地人相信白化症患者的身體部位會帶來好運、財富與政治權力。
其他的迷信還包括:白化症患者是惡靈,是歐洲殖民者的鬼魂,或是女人出軌與白人男性發生關係後所產下的後代。據傳,白化症兒童壓碎的四肢可以治癒任何疾病,要價最高。當一整套白化症患者的身體部位可以賣到10萬美元的高價時,就很容易明白巫醫為何不缺有殺人意圖的打手了。
然而,諷刺又殘酷的是,白化症患者因缺乏黑色素,預期壽命已經很短了。丹尼告訴我,白化症的女性,境遇更糟。因為一些坦尚尼亞的鄉下人相信,與白化症患者發生性關係可以治癒愛滋病。
如今丹尼已成年,他說他不再擔心自己的安危。對於自己老是被當成外人看待的命運,他似乎已經聽天由命,不再掙扎了。
東非白化症患者的困境並非歷史,而是一場默默發生且日益嚴重的人道危機。粗略的估計顯示,2000年以來,遭到綁架與殺害的白化症患者有數百人。一位與我在白化症醫療中心共事的非洲醫生確信,實際的數字遠比那個估計值高。祕密的屠殺是關起門來、在家庭內部進行的。
皮膚是一種實體,就像心臟與肝臟一樣真實,但它同時也有獨特的社交性質。單一基因突變雖然只影響皮膚黑色素的產生,卻可以毀了一個人的人生,甚至害他慘遭他人謀殺。東非的白化症讓人清楚看到,即使考慮到文化與種族,皮膚外觀也很容易淪為一種手段:把他人定義為「他者」,以及用來煽動恐懼及滿足貪婪。
在英國,膚色不需要太黑或太白,只要差異很大,就足以變成分隔你我的關鍵。我記得一位來自伯明罕的巴基斯坦裔女子,她的臉因白斑症而出現塊狀白斑。她談到過去多次的治療經驗,談沒幾分鐘就哭了起來,並斷斷續續提到她可能永遠嫁不出去了。
幾個月後,我遇到一位同樣沮喪的印度婦女,她的臉因為一種叫做黑斑(melasma)的疾病而變得暗黑,臉上對稱地散布著深棕色的斑點。這種變黑的現象是動情素與黃體素造成的,它們會刺激黑色素細胞分泌黑色素。
動情素與黃體素在懷孕期間會大量產生,所以黑斑常稱為「懷孕的面具」,但這位病人並未懷孕。據推測,懷孕期間,身體試圖保護皮膚中的葉酸不受陽光傷害,才會大量產生動情素與黃體素。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女性在生育期那幾年,膚色通常最深。這兩名患者的皮膚都是淺棕色,一個人的膚色變淺,另一個人的膚色變深,但她們承受的社交後果一樣。
「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紅皮爭議」(Redskins controversy)、「好萊塢洗白」(Hollywood whitewashing)。2018年,在短短一週內,這些詞輪番登上美國某大報的頭條。如今的輿論與爭辯比以前更常談論到膚色問題。影響色素沉著的疾病,導致個體遭到社會排擠。但古往今來導致人類之間出現最大分歧的因素,是先天的膚色差異。
為什麼在一公釐厚的外皮上,如此微小的黑色素濃度會造成那麼多的痛苦與折磨呢?誠如第三章所述,膚色大多是由皮膚中黑色素的類型與濃度決定的,這是因為皮膚既是堡壘,也是工廠。章魚般的黑色素細胞分泌黑色素,以避免我們受到UVB的傷害。然而,皮膚也像一塊砧板那樣敞開,渴望那些射線把維生素D前驅物切分成活性型維生素D。
人類開始從非洲與中東那些陽光充足的炎熱地區遷徙到其他地方後,皮膚開始過著走鋼索的生活:在陽光有限的地區分泌太多黑色素會導致維生素D缺乏;在陽光充足的地方分泌太少黑色素會使皮膚的DNA嚴重受損,也會減少體內的葉酸(這是孕婦生產健康後代所不可或缺的營養素)。人類經過數千年的遷徙與調適後,那些從赤道遷徙到紫外線較弱地區的人群,開始出現比較白皙的皮膚。
一張顯示世界各地人類色素沉著的分布圖,幾乎完全吻合美國太空總署(NASA)發布的地球紫外線照射衛星圖。其中有一些明顯的例外,但那些例外更有助於強化這個理論:膚色深沉的因紐特人住在遠離赤道的地方,但他們的膚色深沉很可能是因為,他們以魚和鯨脂為主的膳食中含有特別多的維生素D,彌補了皮膚攝入維生素D不足的影響。
也有可能是因為在夏季那幾個月,他們的深色肌膚可以避免極長時間曝曬紫外線所造成的傷害(而且白雪還會強化紫外線的照射)。
在上述的遷徙過程中,皮膚黑色素濃度的微調,使人類各種族呈現出多種美好又獨特的膚色。人類膚色的多元化是許多基因調節不同類型的黑色素所造成的。膚色淺的人可能產生較多的紅黃色「棕黑素」(phaeomelanin,嘴唇、乳頭、紅髮的顏色來源),膚色深的人產生較多棕黑色的「真黑素」(eumelanin,這也是人類皮膚中最多的色素)。
黑色素細胞被名叫「第一型黑色素皮質素受體」(melanocortin 1 receptor,簡稱MC1R)的小分子包覆起來,這些小分子啟動時,會減少細胞生產的棕黑素,並以真黑素取代。有紅髮、白膚、雀斑的人,身上的MC1R基因大多有突變,受體無法運作。這種基因突變對移居北歐的人來說有好處,因為北歐的紫外線少。如今這種突變仍很常見,尤其是在凱爾特(Celtic)血統的身上。
不過,即使是適應性很強的皮膚,適應全球化的速度也不夠快。如今我們可以在幾小時內飛越很長的距離,但人類皮膚需要幾千年才能適應那麼長的遷徙。近年來移居高紫外線曝曬區(如澳洲),或經常造訪陽光充足國家的淺膚色歐洲人,罹患皮膚癌的風險顯著增加。相反地,深膚色的人移民至高緯度地區,也可能因為缺乏維生素D而罹患骨質疏鬆症、肌肉無力、憂鬱症。
跨大西洋奴隸貿易期間,1200萬名非洲人被迫移到北美,可能是最有名的移民案例。皮膚身為社交性最強的器官,也展現出人性最惡劣的一面,披著歷史的傷痕。皮膚有如一道圍牆,把我們的內心與外界隔離開來,定義了我們,也把他人隔絕在外。皮膚也是人體最明顯的器官,這使皮膚成了一種社交武器,被兩股困擾人類的力量所利用:對身分的追求,以及對權力的渴望。
相關書摘 ▶《皮膚大解密》:除了防曬,目前對於「抗老」有充分證據的成份只有一個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皮膚大解密:揭開覆蓋體表、連結外界和內心的橋梁,如何影響我們的社交、思維與人生?》,臉譜出版
- momo網路書店
- Readmoo讀墨電子書
-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將由此獲得分潤收益。
作者:蒙帝.萊曼
譯者:洪慧芳
「它不只是一張包裹內臟的包裝紙!」科學與人文的結合,一部漫談外表與內在關聯的皮膚之書。
沒有哪個器官是像皮膚這樣,同時扮演如此多重的生理與社會角色。它是抵禦外界的屏障,每天承受無數次的抓扒揉捏,卻不容易破裂。它是無數微生物的棲息地,其上的居民都倚賴它的溫度、濕度、毛髮與流動再它下方的溫暖血液。皮膚是一面螢幕,能及時反映內心的活動,無論是一陣臉紅、冒冷汗或臉上的表情,都將我們的情緒展露無遺。
它也是一本可供瀏覽的書,皮膚的顏色或狀態,刺在上面的圖騰或疤痕,都向我們訴說著血淋淋的歷史,或是每個生命獨有的故事。透過皮膚,我們得以看見科學的驚奇,也得以窺探皮膚如何形塑我們的自我認同,以及它如何影響全人類的歷史、語言和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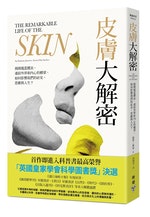 Photo Credit: 臉譜
Photo Credit: 臉譜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翁世航